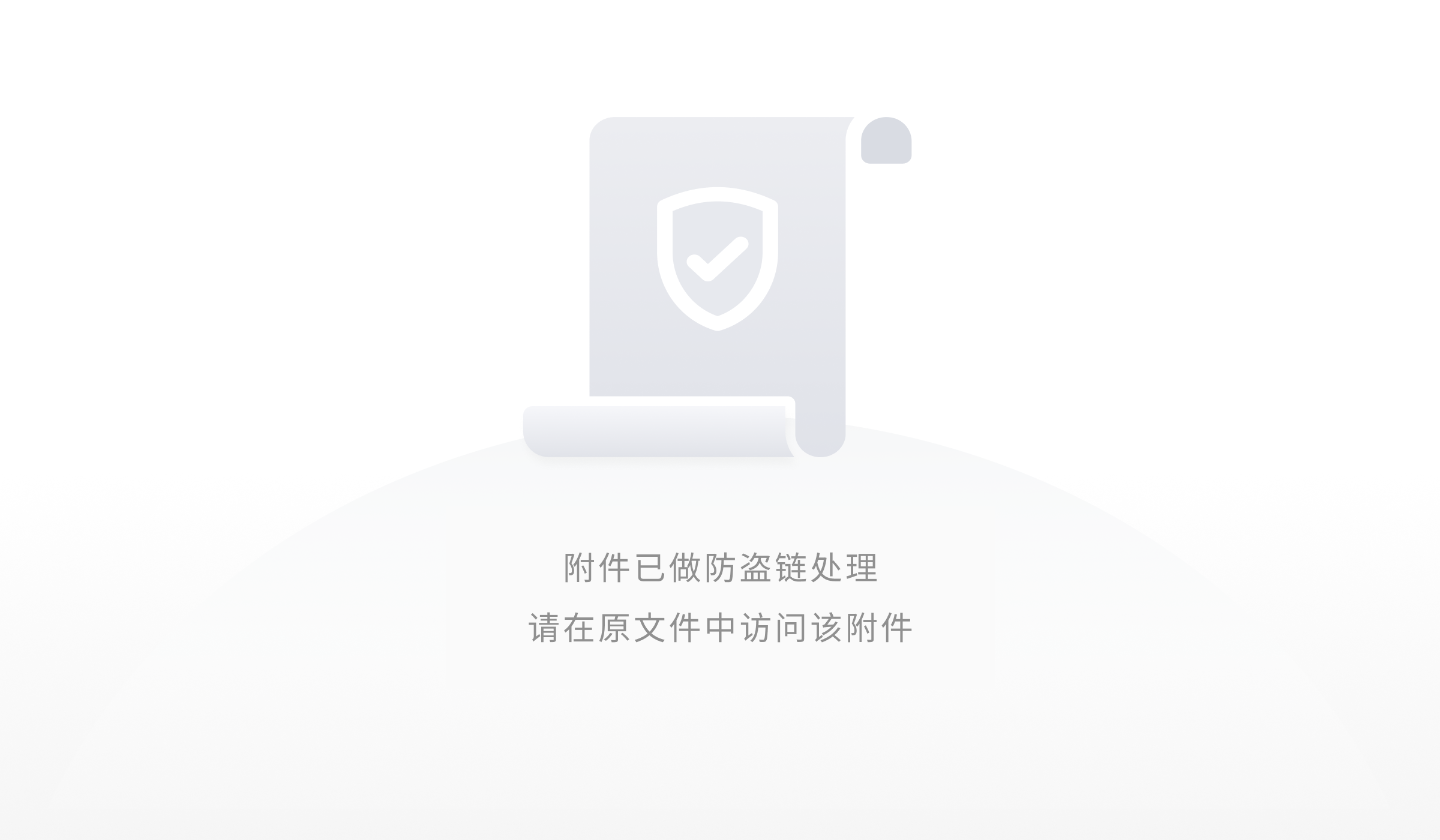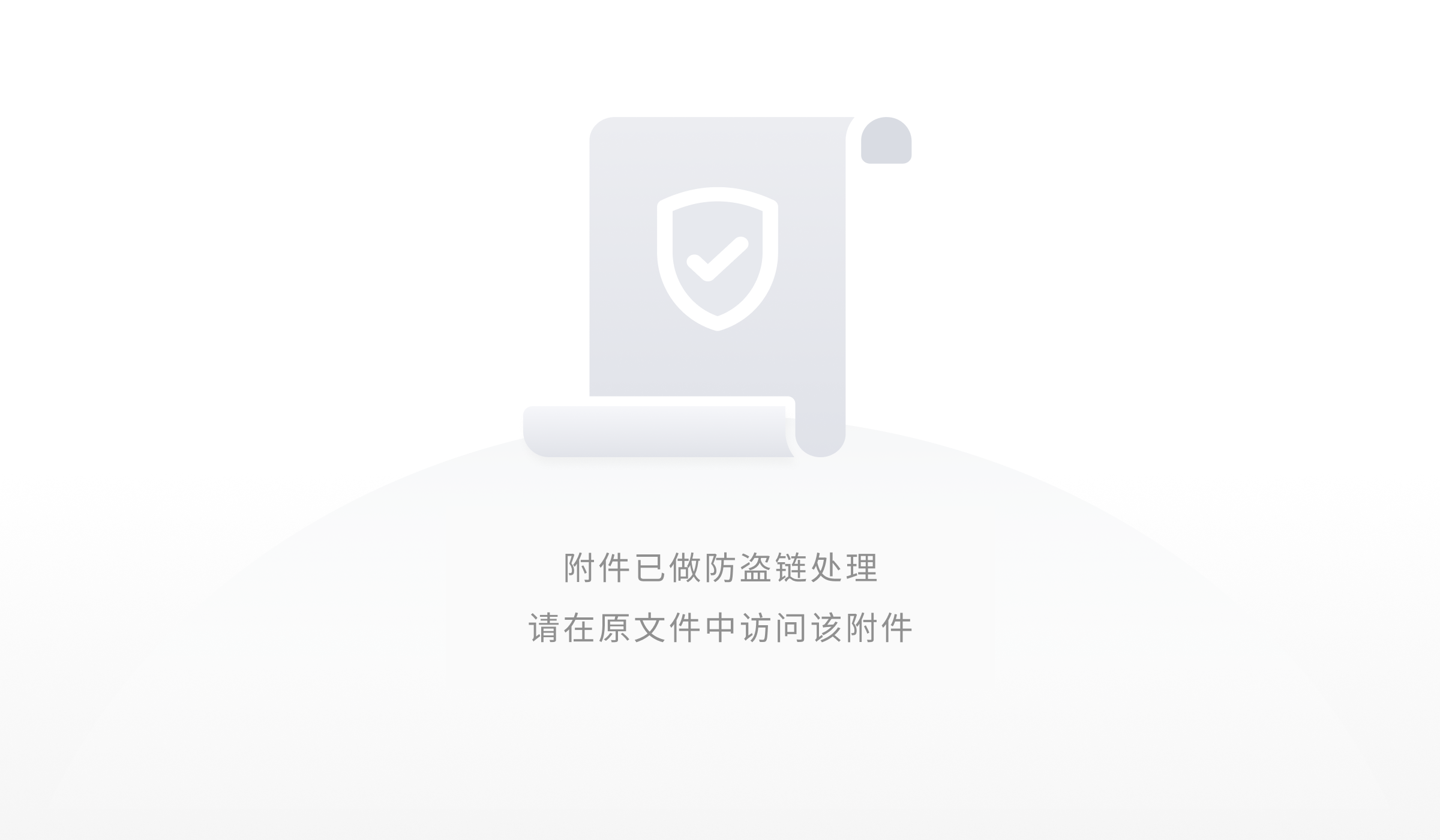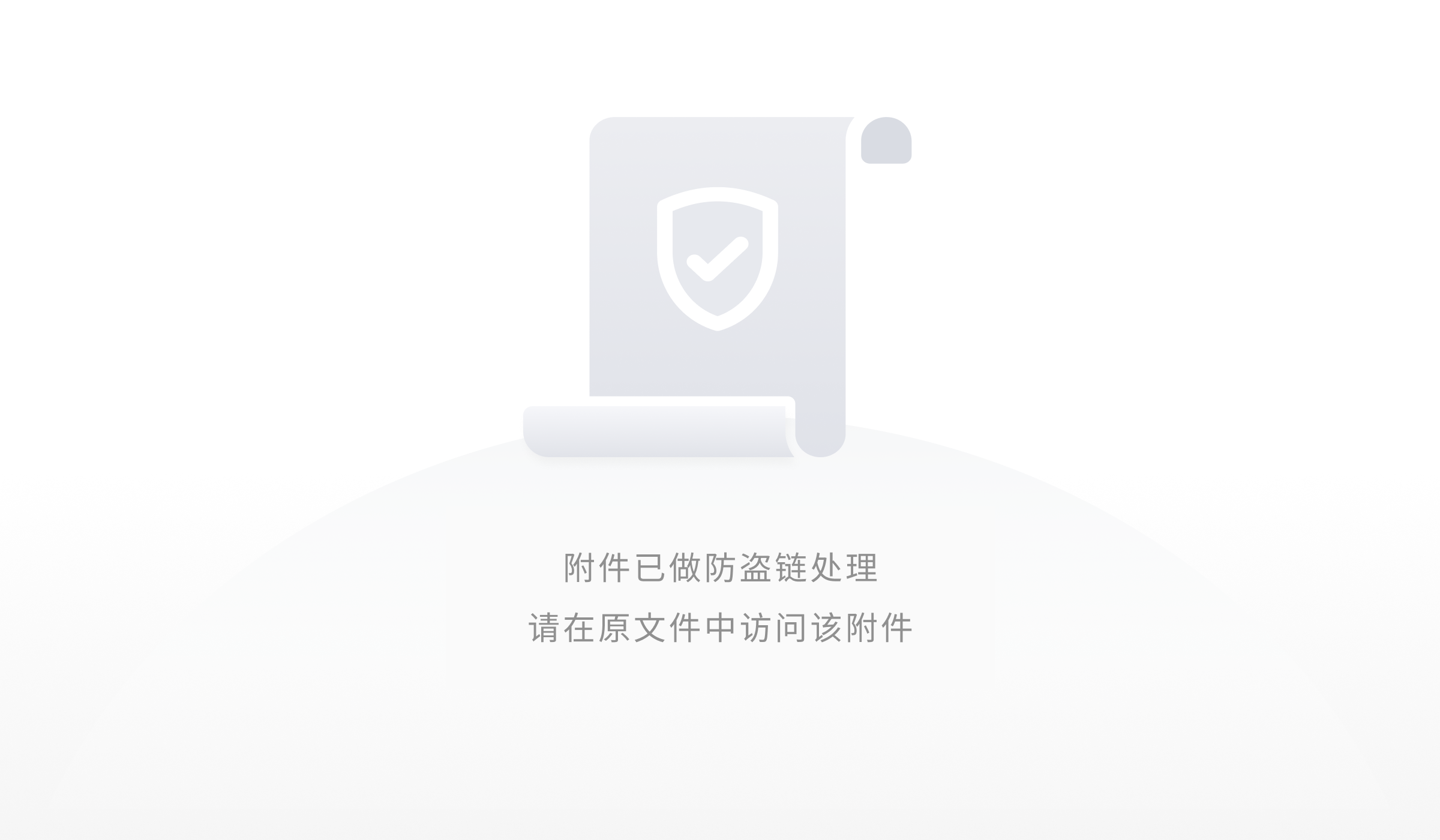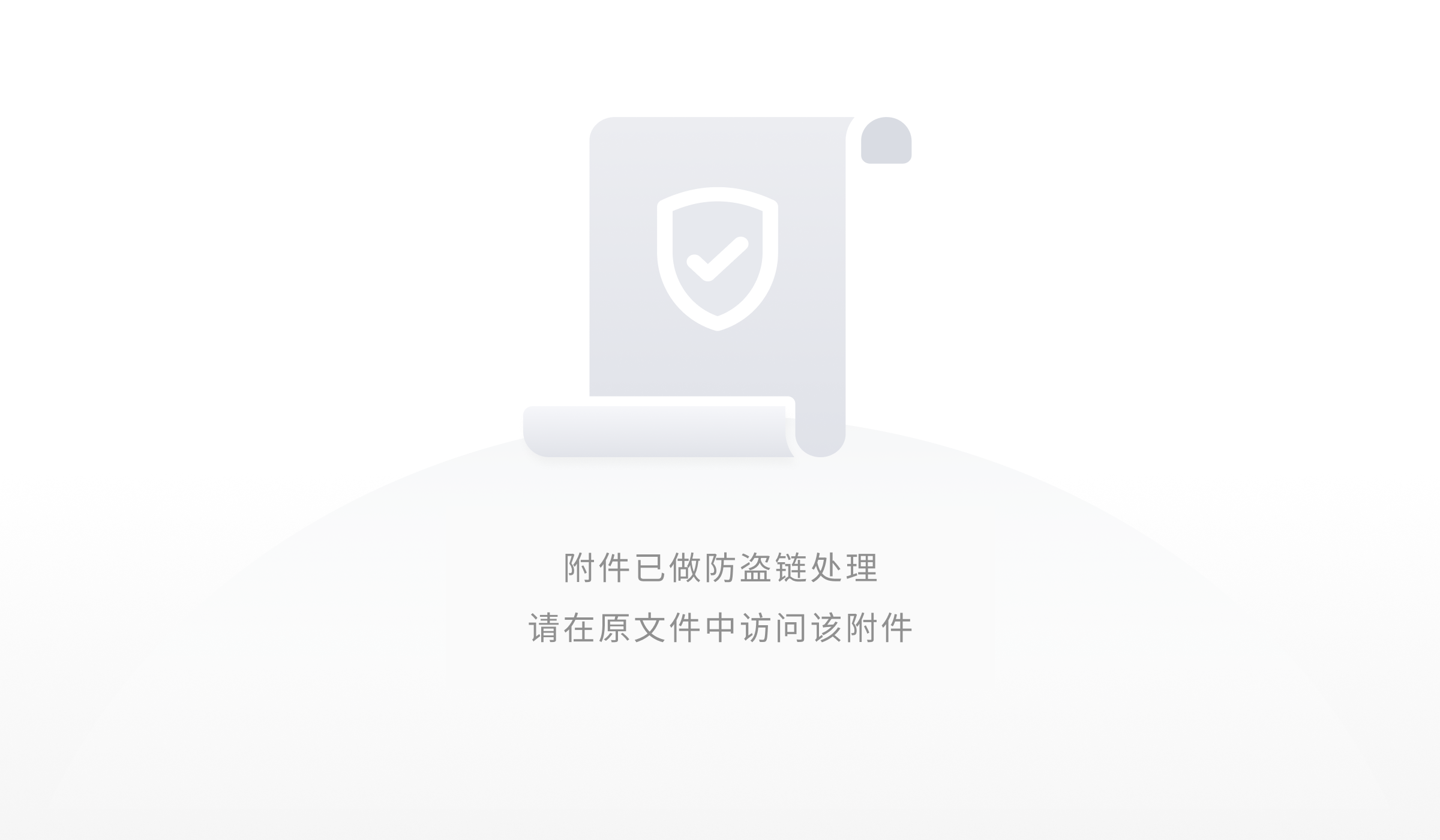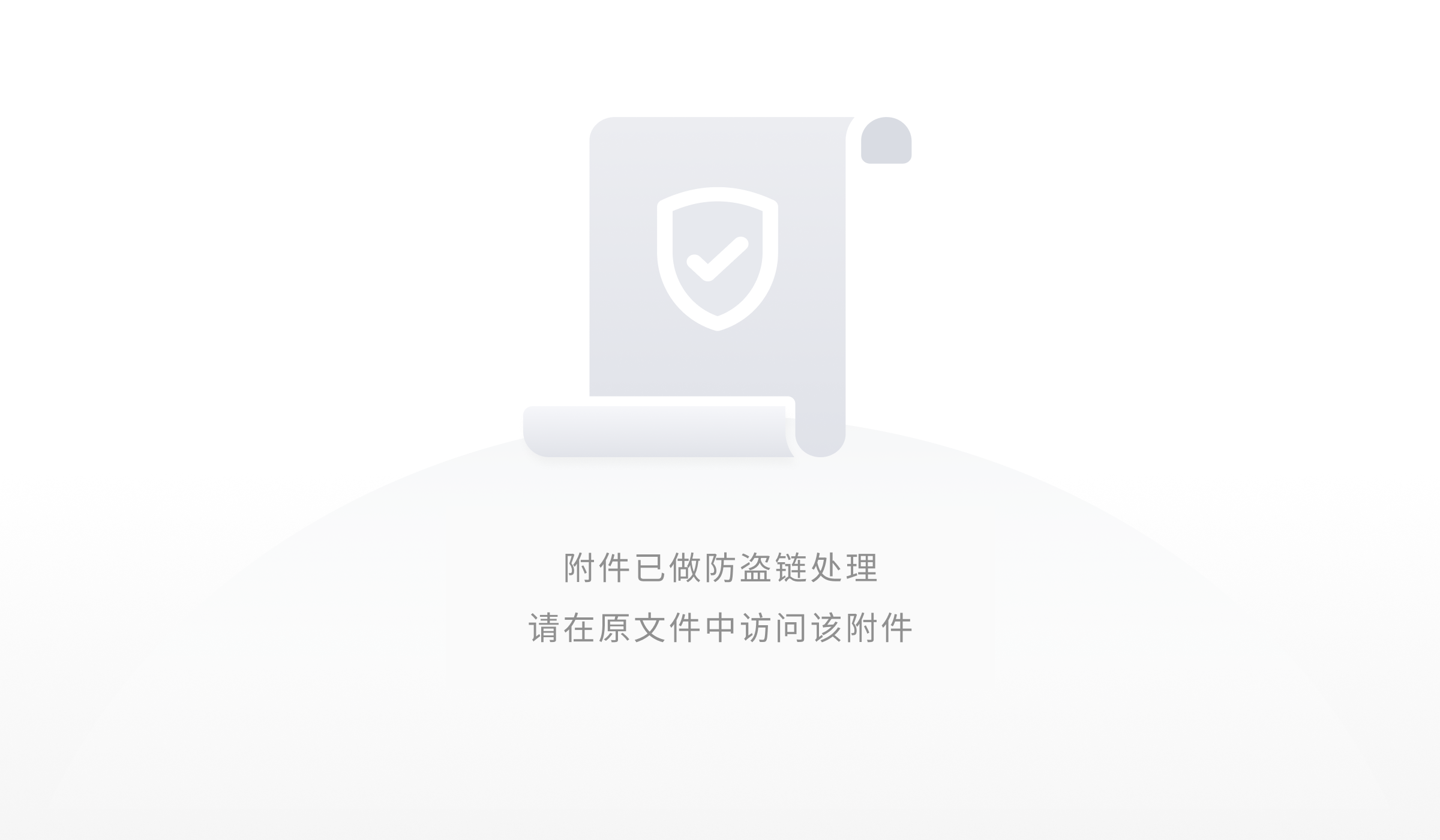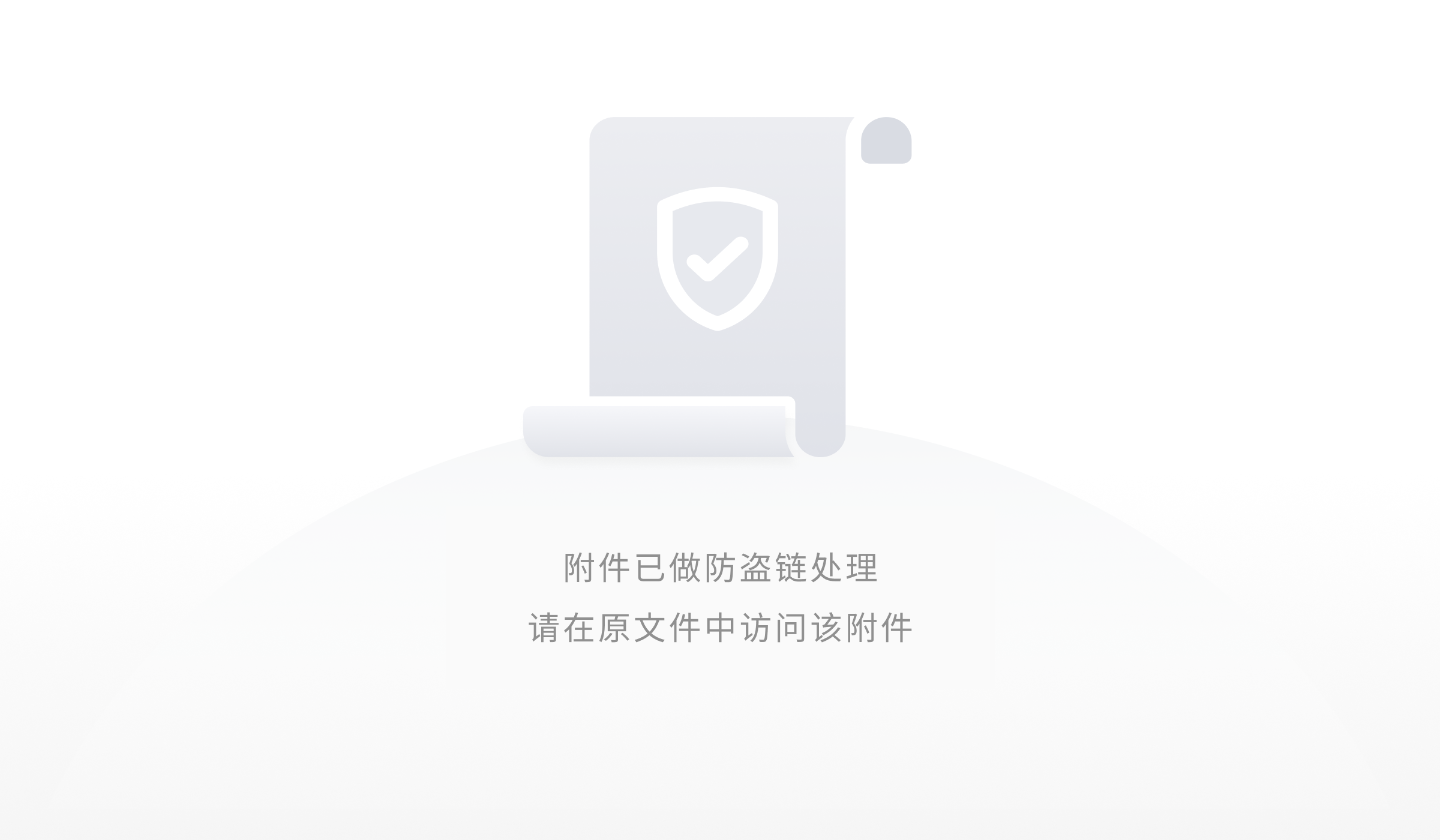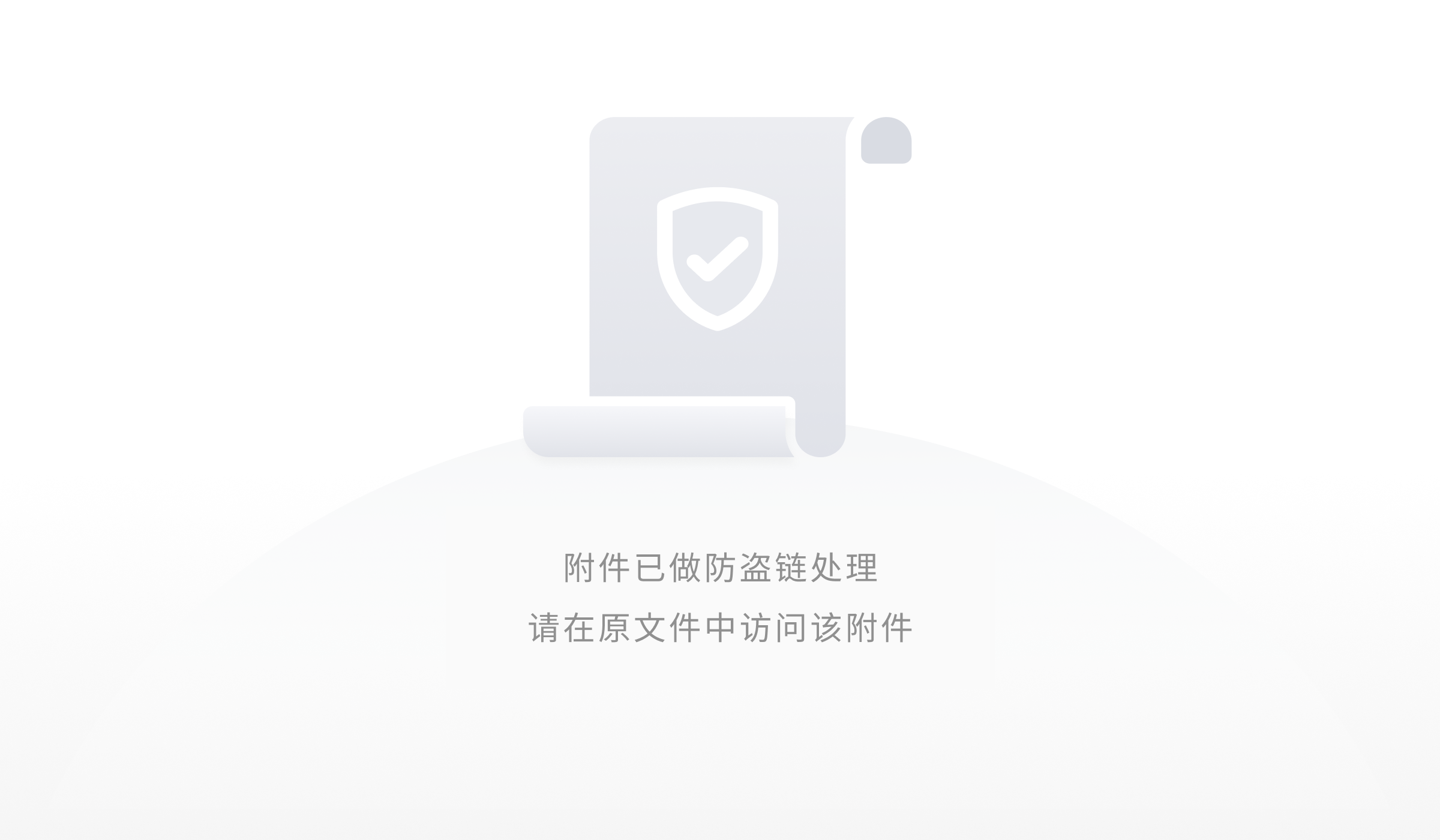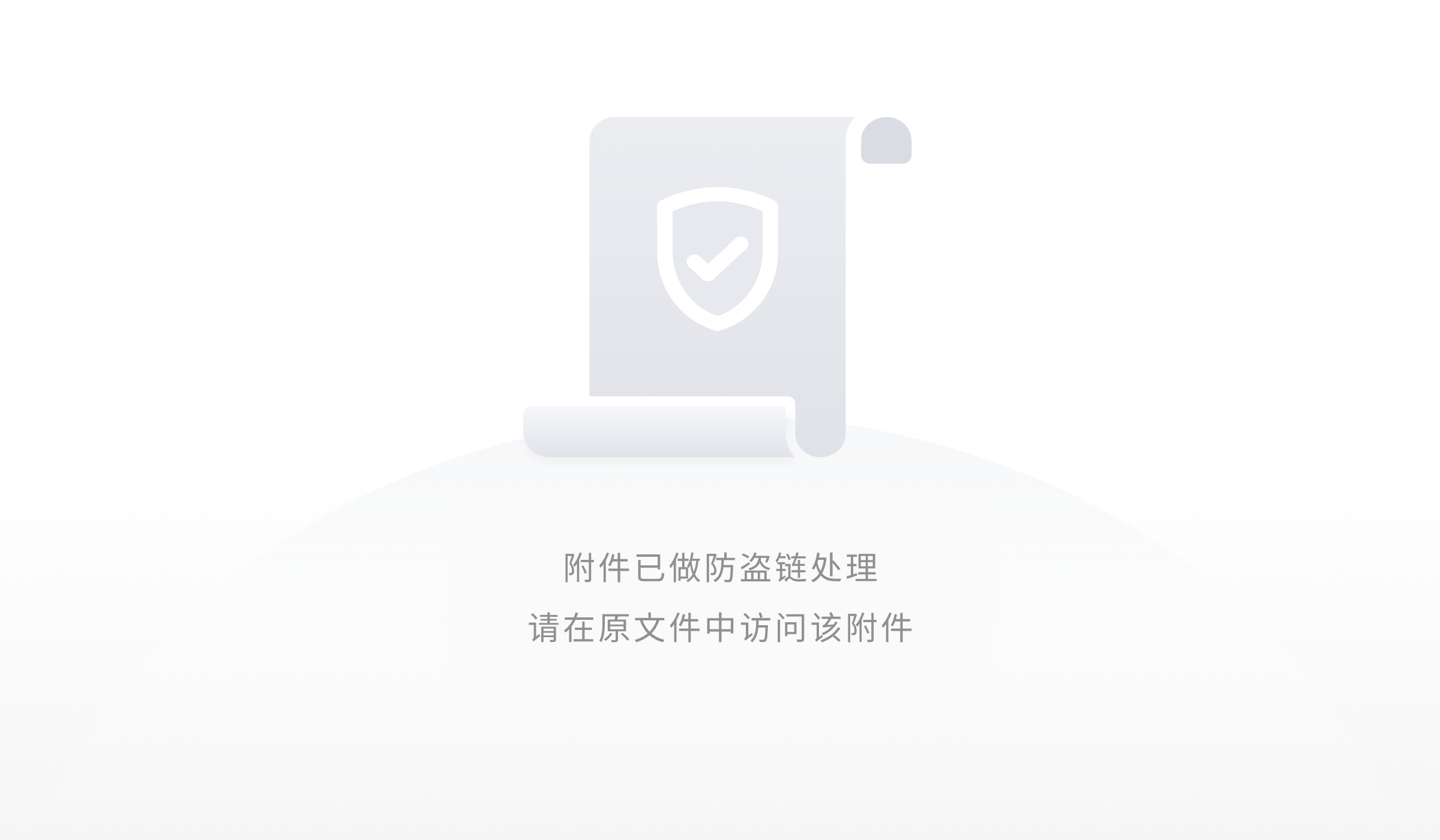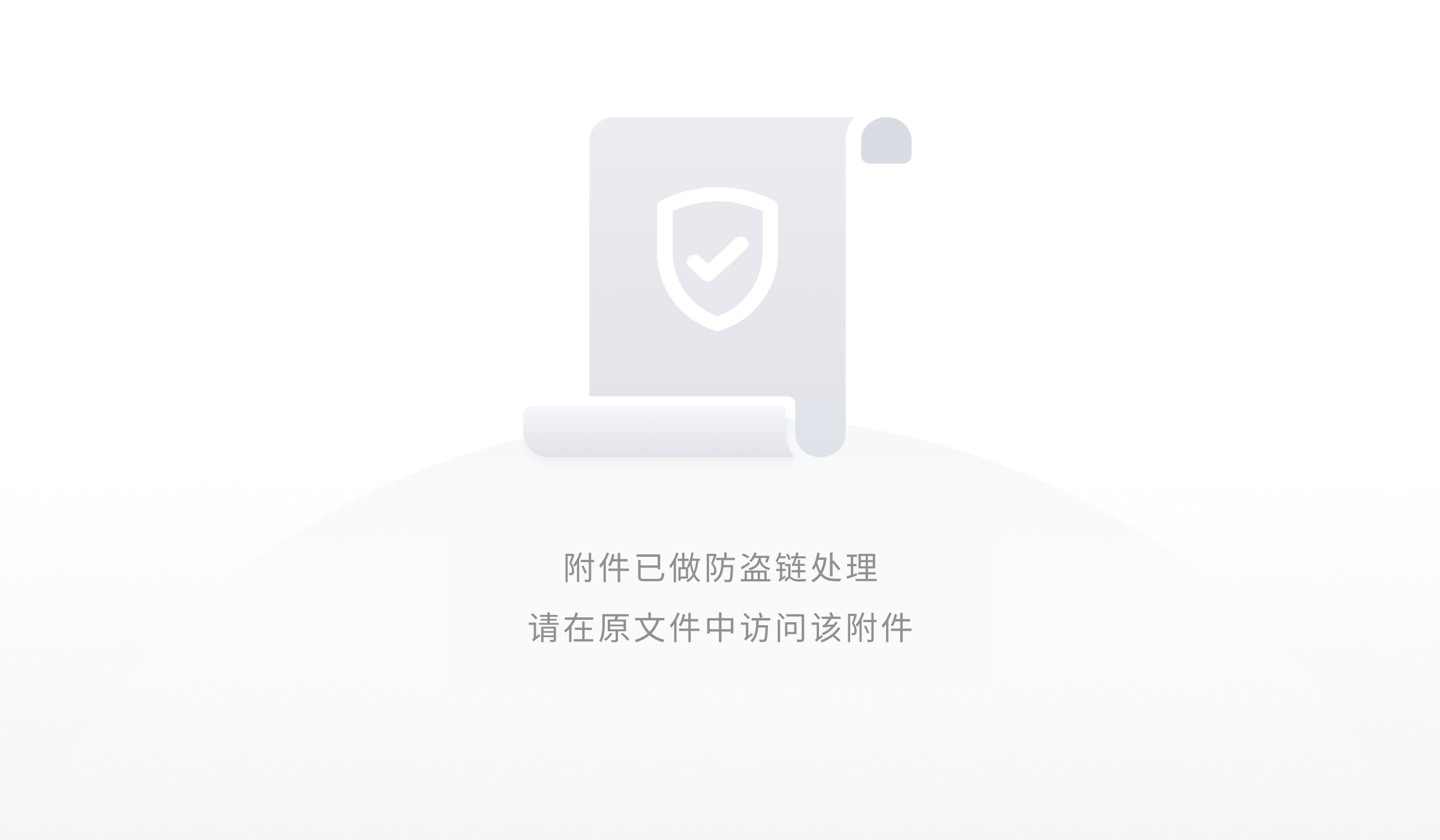- All
- 没有分类
2024.06.14
2023 “滩涂”项目- 作品共创手册
- 姚异姚
- 贾瑛
- Unitrip玎玎
- KC程彦彬
- bo 樊博
- 飞行家
- 邱波
- 巨厦
- 随园
- 框框
- 邱十八
- 张敏
- 柏伦
- (突发事务无法出席)昊:兼职新媒体艺术家,做媒体装置,身体相关的行为表演。毕业于 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平时兴趣爱好,健身瑜伽打泰拳,即兴喜剧。参加过一点阿卡贝拉训练。
- (身体抱恙无法出席)Tai小邰:设计专业毕业。做过公共艺术策展相关工作,大型公共装置等。有过话剧舞台表演的经验,对文字、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有天然的感动,对音乐和自我觉察很感兴趣。
- 信任
- 开放
- 倾听
- 投入
- 第一周(9月11日-9月17日)
- 第二周(9月18日-9月24日)
- 第三周(9月25日-10月1日)
- 人声为主,广场合唱式基于个体感受的集体声音游戏
- 声响雕塑通过声音行为,建立空间能量场域,创造声响雕塑的运动。
- 声音仪式
- 田野漫步实践作曲工作坊广场表演现场能量波动集体谐振
- 今天发出声音是为了什么记忆回响当下所闻未来幻听
- 滩涂之上,一切皆有可能声音召唤空间的行动。
- 聆听
- 想象
- 转化
- 基础热身阶段 (9.11-9.24)
- 聆听热身
- 作曲热身
- 个体田野空间作曲工作坊阶段 (9.25-9.26)
- 集体即兴作曲共创工作坊阶段 (9.27-9.28)
- 现场表演阶段 (9.29 + 10.1)
- 目标
- 建立个体感知关联
- 不必要展开学术研究,
- 方法
-
- 作业
-
- 目标
- 定义
- 方法最基础版
- 方法升级版
- 聆听材料
- 了解场域
- 跟踪运动
- 练习幻听
- 发声实践
- 作业
- 目标
- 定义
- 人声实验(Vocal Experimentation):
- 实验性合唱(Experimental Choral Music):
- 声音诗 (Sound Poetry):
- 方法
- 聆听/观看
- 练习/尝试
- 作业
- 人声实验(Vocal Experimentation)
- Meredith Monk:
- 专辑 <Dolmen Music> https://music.163.com/#/album?id=307005
- 专辑 <Volcano Songs> https://music.163.com/#/album?id=306990
- 演出视频 https://youtu.be/69yOZQ53SLM?si=FKoo5NUXlS6i5HLh
- Hatis Noit
- 专辑 <Aura > https://music.163.com/#/album?id=143787790
- Joan La Barbara:
- <Voice Is the Original Instrument> https://music.163.com/#/album?id=287993
- Yoko Ono
- Meredith Monk:
- 实验性合唱(Experimental Choral Music)
- Annea Lockwood / Water and Memory / Cafe OTO Experimental Choir https://youtu.be/QWPyK4HWuEQ?si=BoWhyEc_V_cKUxW2
- A choral experiment with Sxip Shirey | The Gauntlet at ANTIDOTE 2018 https://youtu.be/vgceFYE1YKE?si=Vsjm4BvKhMRtOj6v
- Jaap Blonk & Others: 专辑 <Five Men Singing> https://music.163.com/#/album?id=160811
- Meredith Monk & vocal ensemble :《On Behalf of Nature》 https://music.163.com/#/album?id=35067037表演视频 https://youtu.be/LjjPL-t9AYM?si=yEC3xPRYbUsnjZ4s
- Meredith Monk 教授人声集体即兴合唱作曲:https://youtu.be/_We3GJUXJh4……?si=ID7iqelCj2Rywi-H
- Stockhausen专辑《Stimmung》 https://music.163.com/#/album?id=124012511
- 声音诗 (Sound Poetry)
- Jaap Blonk
- 表演视频 Jaap Blonk – 2 Sound Poems https://youtu.be/hKJZcapEjHE?si=4mT5cr0iKL4Te3y8
- 表演视频 Jaap Blonk Solo https://www.youtube.com/live/7GltDNnqp74?si=VVW85zeuv2KLvLYf
- Jaap Blonk
-
什么是田野
2. 什么是田野空间作曲
-
- 田野空间:
- 作曲:
- 田野空间作曲:
- 声响雕塑:
- 声音仪式
- 穿过自我
-
如何田野作曲-A:选择空间
4. 如何田野作曲-B:漫游停留
-
如何田野作曲-C:即兴发声
- 在场:以声音进入和联结空间
- 激荡以声音激发和震荡空间
- 合一以声音想象和刷新空间
- 消散以声音赞颂和消解空间
-
如何田野作曲-D:书写记谱
- 定义
- 方法
- 示例
-
田野作曲-步骤C:如何找到可能的声音来源?
- 相信基于聆听的直觉
- 从空间四维度入手感知
- 场所与环境
- 事件与仪式
- 关系与情感
- 身体与物件
- 从时间三维度入手感知:
- 过去
- 现在
- 未来
- 相信基于聆听的直觉
-
田野作曲-步骤C:如何把感知转化为声音?
-
- 吟唱类
- 拟音类
- 腔声类
- 语词类
- 身物类
- 静默
-
-
田野作曲-步骤C:如何敢于发声?
- 呼吸即能量
- 静默即指引
- 张嘴即发声
- 聆听即幻听
- 专注即变化
- 声音即雕塑
- 呼吸即能量
-
工作坊前的热身作业
-
集体工作坊定义
-
- 集体
- 即兴
- 作曲
- 合唱
- 工作坊
-
2. 集体即兴原则
-
- 专注聆听
- Yes…and
- 放开控制
- 创造性回应
3.热身基础练习
-
- :
-
合唱交互分类(四类)
- 一对一
- 一对多
- 多对多
- 所有人:
-
声响分类(五类)
- 吟唱类
- 拟音类
- 腔声类
- 语词类
- 身物类
-
声音即兴方法(六类)
- 随机:
- 模仿:
- 渐变
- 对话:
- 碰撞:
- 编织:
-
合唱中的指挥手势
-
集体即兴作曲架构
- 作曲总体架构:与个体田野空间作曲一致
- 在场:以声音进入和联结空间
- 激荡以声音激发和震荡空间
- 合一以声音想象和刷新空间
- 消散以声音赞颂和消解空间
- 作曲具体内容架构四大块架构下的具体内容,在工作坊上集体创作
- 声响听感
- 声响构成:
- 声响运动
- 空间位置
- 作曲总体架构:与个体田野空间作曲一致
- 二十五日工作坊安排
- 目标
- 开场(1:00-1:20)
- 交流(1:30-2:30)
- 田野 (2:30-3:30)
- 作品 (3:30-5:00)
- 目标
- 二十六日工作坊日程
- 目标
- 热身(1:00-1:15)
- 田野 (1:15-2:00)
- 作品 (2:00-4:00)
- 交流 (4:00-5:00)
- 目标
- 二十七日工作坊日程
- 目标
- 热身(1:00-1:15)
- 交流 (1:15-1:30)
- 作曲 (1:30-5:00)
- 目标
- 二十八日工作坊日程
- 目标
- 热身(1:00-1:15)
- 交流 (1:15-1:30)
- 作曲 (1:30-4:00)
- 预演 (4:00-5:00)
- 目标
——————–工作坊产出 —————–
关键问题:你为什么发声?经过四个部分的声音仪式,你从何处切入,以怎样的声音召唤空间?
A. 在场:以声音进入和联结空间
聆听,以声音进入和联结空间。找到自己与空间建立关系的可能声音,尝试发声,并依据感受调整优化,逐步进入空间,形成联结的能量场域,由此架设声响雕塑的底层基础。
- 历史回响
- 现实压抑
- 自然生命:
- 资本都市
- 文语糅杂
- 旅行景观
B. 激荡:以声音激发和震荡空间
聆听,以声音激发和震荡空间。跟随空间中的不同声音,模仿并不断改变它,拆解挪移转化,创造出空间空隙,使得能量四处流动,让声响雕塑的轮廓逐步显现。
- 历史回响
- 现实压抑
- 自然生命
- 资本都市
- 文语糅杂
- 旅行景观
C. 合一:以声音想象和刷新空间
聆听,以声音想象和刷新空间。以想象中新空间的可能声响,融合或遮蔽现有声响,自我-声响-空间合一,在不断重复运动中能量加强,演化为新的结构,声响雕塑由此清晰显现,幻化为新空间。
- 历史回响
- 现实压抑
- 自然生命
- 资本都市
- 文语糅杂
- 旅行景观
D. 消散:以声音赞颂和消解空间
聆听,以声音赞颂和消解空间。以轻柔声响渗入空间,能量柔和四溢,声响雕塑消散藏匿于周遭,于建筑/水/身体/草木等等各种,直至空间消散。
- 历史回响
- 现实压抑
- 自然生命
- 资本都市
- 文语糅杂
- 旅行景观
- (身物)
- 张敏:
- 随园:。
- bo 樊博:。
- 框框
- 玎玎
- 巨厦
- 飞行家
- 姚异姚:。
- 贾瑛:
- 柏伦:
- 邱十八
- 邱波
- KC程彦彬:。
- “在场”:以声音进入和联结空间(让自己变成一个声音,与空间建立联结)
- PART A:独立进入与自然重叠
- 声响运动(一对一) 间或出声自然重叠清晰有力
- 声响听感(不同浪头,以各种形态,往滩涂拍打过来)。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不使用身物
- PART B:三声部轮替与单声高空划过
- 声响运动(一对多) 持续发声能量稳定输出从高处高能量划过
- 声响听感(浪头适度汇集,偶有海鸟顶端划过)。克制和秩序感自由的,拉开的,醒觉的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不使用身物
- PART C:嘘声清耳
- 声响运动(所有人)
- 声响听感(浪头冲击滩涂前,短暂风平浪静时刻)。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
- PART A:独立进入与自然重叠
- 激荡以声音激发和震荡空间
- Part A:对话碰撞与张力强度
- 声响运动:(对话碰撞
- 声响听感(不同的浪头,以自己的狠劲儿,持续的拍打和冲击滩涂。滩涂不断被冲刷掉一些现有的部分,显露出被遮蔽的一些部分)。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声响库即兴声响
- Part B:身物响起与噪声带刷过
- 声响运动:(所有人) 叠加在Part A的持续声响中
- 声响听感(被不同浪头冲刷拍打的滩涂,被一阵强风扫过,或者一抹长长的阳光扫过)。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
- Part A-B:持续3-4个来回。
- Part A:对话碰撞与张力强度
- 合一以声音想象和刷新空间
- Part A:编织与刷新
- 声响运动:所有人模仿渐变编织模仿变形,编织
- 声响听感(浪淹没堤岸,覆盖滩涂,弥漫四处,一波接着一波)。
- 空间移动
- 声响类型
- Part B:呼吸与衔接
- 声响运动:所有人
- 声响听感(浪开始停歇,轻柔晃动)。
- 空间移动
- 声响类型
- Part A:编织与刷新
- 消散以声音赞颂和消解空间
- Part A:气息与颂唱
- 声响运动
- 声响听感(仿佛所有的浪都停歇了,保持轻柔的晃动)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
- Part B:水泡与器物
- 声响运动
- 声响听感浪逐渐褪去,滩涂之上,最细微之物,发出了自己的细碎的声响,但是能听得到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
- Part C:低吟与口哨
- 声响运动
- 声响听感浪和滩涂都消散了,如泡沫般)
- 空间移动
- 声响构成:
- Part A:气息与颂唱
- 飞行家
《外滩.滩涂》
- 玎玎
- 姚异姚
滩涂
- 随园
- 邱十八
- KC程彦彬
- 巨厦
2024.06.14
2023 “滩涂”项目 – 概念介绍及工作坊招募文本
Hi,大家好,
我是张安定(Zafka),创作声音艺术,也做实验音乐。这个九月,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在靠近黄浦江边,外滩美术馆所在的小广场空间,做一次集体的户外演出,以我们的声音与想象,来转化此处的空间。
这是一个以人声为主,广场合唱式的公众参与作曲与表演项目。我希望能找到10-12位同行者,用四天的时间,集体创作并表演一个三十分钟左右的作品。这里的合唱,并非传统的人声合唱音乐,而是更为自由与实验的使用我们的声音以及身体。这里的作曲,也并非传统音乐作曲,而是指对整个声响以及仪式的结构化过程。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的话,请继续往下读,我会详细介绍目前项目的设想。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我,也可以访问我的个人网站zafka.cn。欢迎你来参加,一起完善、优化以及完成这个项目。
一)项目概念
我把项目命名为“滩涂”。外滩不只是建立在河海之交的滩涂之上,也是矗立于历史的滩涂之上。外滩是上海人的外滩,也是更多人的外滩。身处目前之时局,很多东西被淹没,很多东西又重新显现。我们如同徒步在滩涂,在现实未来与历史交错之中,听到风声与呼吸,希望与忐忑。
因此,以外滩以及所处建筑空间为场域,所进行的集体广场表演,将是一次藉由声音召唤空间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曾无数次的面对虚空大地,巨灵猛兽,以自己的身体,声音以及物件,组合成各种方式,集体展开召唤,唤回隐匿于现实和想象中的种种可能性空间,就此重塑我们当下所处的时空。
此次的项目,参与者将把自己对外滩场域的个体感知与想象,转化为多样的声音与行动,并集体转化为新的仪式,以亲身表演的方式,召唤空间,重塑此地时空。
因此,空间-历史-记忆-情感-想象,这些个体感知,皆为集体作曲所指向的部分。这些感知,在现场通过参演者,呈现为数字,物件,名字,吟唱,呼喊,节奏,声响,身体形式,空间位置等等,在建筑空间-环境声响-人群交互之中,有机的分散,行进与涌动。
由此,在表演现场空间的能量波动之中,声音与身体的生产之中,声音召唤空间的仪式之中,这一切皆转化为滩涂之上的集体谐振。
二)项目方法
那我们如何展开本次的集体创作,将个体感知与想象,转化为集体的声音表演呢?
首先,我们需要在田野中展开工作。项目的创作和表演,都将在外滩美术馆所在的广场户外区域展开。我称之为“田野剧场”。从田野中来,重新回到田野。但这并不是建立在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田野,也并非建立在参与式艺术行动上的田野。这种田野方式,更关乎田野呼吸,直接指向个体的体验,想象与写作。重要的是把个体的田野感受,以作曲架构的方式重新带回来,以集体的身体现场,剧场化的重新释放到田野空间之中。
其次,在田野中具体的创作方法,我称之为“空间田野作曲方法”。不同于具象音乐的采样与调变,不同于声音艺术中常见的声音漫步聆听与录音,也不同于传统音乐的田野采风与音乐化,空间田野作曲方法,源自我基于人文地理学所设计的“地方音景田野观测表”。这是一整套田野感知与行动方法,由几十个具体而微,激发感知与想象的问题构成,也覆盖了最终作曲所需要的几类关键维度的素材。参与者以此作为作曲素材生产的工具,以田野漫游的方式,基于外滩建筑空间与历史感知,产生大量个体化体验数据,形成集体作曲与现场表演所需要的核心素材基础。
再次,我们将依据“集体即兴作曲工作坊”来结构化田野所积累的素材。我们以工作坊的形式,以声响展开对话,在对话中形成新的仪式与整体结构。基于一定的规则,田野素材重新融合与再创造,在现场空间中相互响应。这样集体创造的过程,同时是最终表演的预演排练过程。
最后,项目的现场表演,将以“半即兴现场”的方式展开。表演其实是能量的产生过程。以声音召唤空间为名,参与者以自己的个体数据为谱,按照一定的作曲结构,在现场自由响应,自由行动,群体即兴进行表演。每个参演者都拥有某种主动性,同时我也将作为参与者,于其中指挥与现场实时互动。
三)项目设计
项目包括五个环节:1)招募沟通;2)预热准备;3)田野漫游;4)作曲工作坊;5)广场表演。
1)招募沟通:参与者通过添加艺术家微信,沟通基本情况。之后艺术家将与初选合适的申请者电话沟通,进一步相互了解。这将需要您30-60分钟时间。
2)预热准备:参与者都确定之后,我们将有一次两个小时的线上会议。我将介绍项目情况并答疑,项目团队相互熟悉,以及提供给参与者一些预热小作业。
3)田野漫游:9月25-26日。两天时间,我们将一起在外滩区域聆听,感受,记录,转化,交流,最终形成每个人的作曲素材库。
4)作曲工作坊:9月27-28日。两天时间,我们将在一起展开作曲工作坊,结构化整个表演,并进行排练优化。
5)广场表演:9月29日上午,我们戴设备现场彩排。10月1日下午,我们将进行2个场次的演出。
四)参与方法
我们需要招募10-12人左右。当然,我们不需要有专业的合唱以及其他音乐基础。如果有,也挺好。如果你有艺术或音乐相关专业训练,或具有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训练背景,也很好。
除此之外,对于参与者,有以下的几点共同的小要求:
1)感知敏锐,头脑开放。因为创作和表演过程,都需要我们在田野之中,敏感于自切身的感知,想象,以及集体的聆听与回应。
2)时间充裕,守时守信。因为创作费事费力,并不容易,何况又是一次集体的行动。
3)不怯场,敢发声。因为我们需要面对公众,以自己的声音和身体,放松展开表演。
如果您有意,可以按照以下报名方式参与:
添加微信soundzafka,注明“RAMA项目参与”。通过后请初步自我介绍,感兴趣参与原因,以及电话联系方式。
微信沟通之后,如果初步双方都觉得合适,我会电话联系您,并做进一步相互了解。电话沟通之后,我会依据总体情况,决定参与者人选,并通知您是否入选。
参与者在以下时间段需全程参与:
工作坊:9月25日-9月28日 14:00-17:00
彩排: 9月29日 10:00-12:30
两场演出:10月1日 16:30-17:00;17:30-18:00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9月20日
参演补贴:500元/人
2024.06.14
2023 梦见…
(2023.12.02)梦见一众人徒步下山入村。误入村庄内某庭院木屋。屋内宽敞,数十桌摆开,疑似饭庄。每桌之上,自屋顶横着悬吊一捆干草,以铁链束其两段,以白布包裹干净。每一干草包上,均插有一细铁支架。架上绑缚一猫,体态舒展,不得动弹,手里捧着一条被啃食的鱼。另外又有若干大桌。桌顶悬吊干草包外并无支架与猫。但每过一会儿,就会有一只身型极为硕长,如猫一般有皮毛的活物,从虚空中出现,紧贴着干草包转上几圈。如同盘龙柱。当地人说,它们叫巨灵。
(2023.11.04)昨夜闭眼入睡。在虚空里看见,许多黑色的细枝桠,开有金色镶边的花,无根无壤,微颤悬于前方,触手可及。很好看。到今天这会儿,还记得清楚。
(2023.10.10)梦见孤身去往高原。岩石,天空,海洋,山脉,宛如切片。于旅馆静坐远观,清晰窥见其中纹理,色彩时时流动。打开管盖,随身携带的绘制颜料,难以抑制的跟随世界的晃动下坠。手腕不自主的一再甩动,好像只是为了与远方的海浪与山峰同频,在房间和纸张上重叠画下一个接一个的曲线。离开旅馆,在路途遇见到一位许久未见的友人。拥抱再三,一而再再而三。身体弯曲晃动,犹如远方岩石的纹理。
(2023.08.20)昨夜梦见有仪轨。黄金色中文和藏文双语,四句两排,整齐有序,悬挂于无边黑色的虚空中,若隐若现。平息静观,拉近焦距,中藏文字体清晰。藏文不识。中文语义深奥,初看似为错乱之字句。只有个别句部分能懂,但醒来已忘。自看到仪轨的一刻开始,瞬间进入清醒梦状态,于睡梦中观看自己此刻的梦境。之后,虚空幻境中有一撑天古树,异常巨大,抬头望不到树冠。众人称之为茶树。树上结满了多肉植物般的手掌般大小茶花儿,厚厚的花瓣儿,浅淡却颜色纷繁不一。众人顺草坡而下,高低次落,摘花而食。我吃了几瓣,唇齿皆香。醒来还记得。
(2023.07.24)梦见灰暗遍野的废墟之上,当空悬置两个巨型物体。一颗略带血橙色橡胶质感光滑透亮的心,一道深蓝色丝绒包裹的铁锈金属体闪电。
(2023.04.25)昨夜梦见深潜入水中,水体通亮,一口呼吸绵长。又与陌生人一起野外长游数十公里,直至无人废弃的景区。在崖高的水岸歇息,看沙土化为兔与龟,纵身入水,复归为沙,又化为龟兔水中嬉戏。梦幻如影之际,摸到水岸沙土中藏有一小型录音机,屏幕显示持续录音已经超过一天,正是自己昨日遗落的机器。
(2023.03.14)梦见目视自己沉睡,呼吸均匀。自唇齿间呼出一个气泡,随吐纳温和生长。一点点包裹身体,房间,屋子,小区,街道…… 愈来愈大,最终将整个虚空纳入。不增不减,不疾不徐。醒来之后,仍然记得气泡一张一弛之间的柔软质感。
(2023.02.15)今晨。梦见有墓冢一处,自地面与墙融为一体。近观之,形似一侧卧僧人,布衣散落纹路凹凸有致。旁人称之为“葫芦布袋和尚”。心疑,何为葫芦?再向前几步仔细端详,原来僧人并无清晰面目,肉身似葫芦一只。
(2022.12.02)梦见京郊有一野山。山顶有数百日裔少年聚集,临空面壁,蹴鞠玩耍。下山道陡峭,至山腰处豁然开朗。荒野之中有一露天街区。灯光暗淡,人声鼎沸。近千青年搭桌吃饭饮酒高谈。奇装异发,口音各异。瞥见后巷有摩托党数人。尾随而入,拾得徽章一枚。席间听闻,此地乃魁翁所建。其子杀人,藏于郊野。此山遂成不良青少年聚集之乌托邦。又见自己于梦中,以纸笔记录此梦,笔痕力透纸背。
(2022.11.24)梦见有大陆悬空,飞船疾驶。景观如碎片落入手机屏幕。又见陆上有学校一所,巨型柳树上孩子们抓住枝条旋转散开,周而复始。树下有众人演出。我手持吉他即兴演奏,大声吟唱,迷幻之调,北印度之风,气息持续不断。
2024.06.14
2022 身体与心智的异种格斗(文:李如一)
身体与心智的异种格斗 (文:李如一)
*本文是李如一为 张安定的“大平原:四个时刻” 4CD套装出版,所撰写的专辑内页文章
张安定不安定。
他语速不算快,但只要一开口,意识就从中汩汩流出,仿佛在用嘴思考,又仿佛在即兴演奏。在我认识的中国实验音乐家里,他有着最入世的性格与兴趣。主修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的他,第一份工作是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担任编辑。二〇〇六年前后,三维虚拟世界Second Life兴起,他很快成为玩家,又加入了国内类似的初创公司。几年后更创办了聚焦青年群体与青年文化的研究和咨询公司「青年志」。对音乐的热情虽未因之减少(毕竟音乐是青年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正式重启音乐创作是近年的事。
一九七九年,张安定生于湖南益阳附近的小县城宁乡,小学二年级时移居益阳。他在宽松的环境下长大。高中时和同龄男生一样痴迷足球,也开始听音乐。「外国的不多,有Michael Jackson和Roxette(笑)。国内的主要是魔岩三杰、指南针乐队、Beyond和太极。」一九九六年,他考入了以收纳「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著称的上海复旦大学,音乐眼界迅速打开,并很快与盟友们组建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乐队(后改名为布拉格)。和许多摇滚青年一样,玩乐队最初的驱动力来自力比多。「一开始就是乱玩,在女生宿舍楼下喝酒唱歌什么的。」但是这种仅靠木吉他伴奏的民谣弹唱很快令他厌倦,「那时其实无关音乐,只和『歌』有关。后来听得多了,又不断买音乐杂志来看,逐渐就对歌丧失了兴趣,开始关注音乐本身。」很快,张安定的聆听对象从披头士跳到了Nirvana、Sonic Youth、梅西安、与勋伯格。布拉格最初还试着排练Nirvana和Sonic Youth的歌,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写原创作品。「布拉格的记忆确实属于青春时期,是难以磨灭的。我们的风格主要是噪音即兴和后摇。两者都发自对声音织体以及不同情绪状态的兴趣和探索。当然,我对于乐队这一形式的舞台感和半即兴演奏所包含的身体性也很感兴趣。布拉格的唱片都是在录音棚半即兴实时录音完成的。」
在没有任何音乐训练的前提下,吉他噪音是一个纯器乐与声音爱好者的自然选择。据张安定回忆,在一次纪念Nirvana的音乐会上,拒绝翻唱的布拉格飙出的无调性噪音即兴表演让他们在圈中获得了极糟的名声。这种以本能、直觉和力比多为先导的创作模式对于年轻音乐家顺理成章。不过在张安定身上,它发挥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在复旦读完本科与研究生后,他前往英国继续进修,音乐创作一度中断。二〇〇四年归国在广州工作,结识了钟敏杰、林志英等声音艺术家,开始关注更注重声音聆听行为以及声音本体的创作。和布拉格时期一样,这一兴趣迫不及待地进化成创作实践。尽管放下了吉他,蹲在笔记本电脑前钻研各类软件的张安定依旧没有舍弃对本能与直觉的信仰。这立即给他的声音艺术作品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风味。二〇〇五年前后,在广州一场声音艺术演出后的讨论会上,我和张安定有如下对话:
张安定:……走在马路上听见汽车很有律动地叫了几声,你觉得「啊,真棒!」,觉得这就是一种音乐性。当你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用它作一件作品时,它为什么不能称之为音乐呢?
李如一:我基本同意,但想补充一点:这种聆听并不是出于本能,而是艺术史发展的结果。如果路易吉·鲁索洛在上世纪初没有发表那篇《噪音的艺术》宣言……
张: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李:如果你生活在十九世纪,我不认为你会觉得那些声音真棒……你似乎认为对噪音的喜好可以是一种自发的东西,可以是根植于我们身体内部的。我认为不是,这绝对是大量阅读的结果,是艺术史发展的结果。
张:我不觉得,我强烈反对。
对话后不到一年,张安定做出了一首令人惊艳的电子原音作品「When Hong Kong Harbours London」。事后回看,这仿佛是对他上述立场的一种佐证。他作为电子原音音乐新手所达到的圆熟感与完成度固然惊人,但此作真正的独特价值在于情绪感染力——一种在电子原音音乐里罕见的东西。这里有他早年乐队经历带来的对声音织体的敏感,以及对乐曲结构的控制力。与此同时,它也宣示了他在上述对话中的坚定信念,即对声音的感受与喜好确实应该来自身体内部。如标题所示,此曲使用了他在香港街头所做的实地录音。从这样一个充满各类著名文化符号的城市取材,很容易落入明信片化的窠臼。张安定回避这一陷阱的方法是抽空实地录音背后的所指,采取acousmatic而非具象音乐的聆听方式,同时将身体本能前置。
两年后的二〇〇八年,张安定在美国厂牌Post-Concrete以数字形式发表了专辑《雍◎和》(二〇二一年由北京的赛剋克厂牌以CD形式再版)。它可以被视为「When Hong Kong Harbours London」的扩大版。同样的创作手法——对拥有特定文化价值的城市空间的声响勘探与重构——从南方的前殖民地移到了北京雍和宫旁的胡同。值得注意的是,这回张安定的前期调研做得更加严谨。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胡同周边游走,用照片和文字详细记录现场,有时会精确到一条小巷的具体宽度。在我看来,这是他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媒体工作的影响。一方面,他在处理新课题时能很快掌握切入的方法;另一方面,每次创作又相当于一次书写与记录。《雍◎和》可以被视为一篇用声音书成的诗性非虚构写作。我们可以想像,若他延续了在报馆的工作,这件作品完全有可能以文字形式落地。
但张安定不安定。在二〇二一年的一次播客访谈里,他表示做完《雍◎和》后就觉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以不用再做电子原音作品。乍听这是个奇怪的说法,仿佛对某种音乐风格的掌握即标志着实践该风格的终点。但我想这一告别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于这种创作方法的不满。无论「When Hong Kong Harbours London」还是《雍◎和》,其创作手法都是相对静态的。与其说是音乐创作,它或许更像调研与科学。实地采录声音是需要耐性的蹲点作业,而当他带着录音回到电脑前时,等待他的是多轨音频处理软件的时间线。对大量声音素材进行挑选、调变、裁切、腾挪、排列组合,几乎就是创作过程的全部。固然,艺术家对声音的敏感度与品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张安定的乐队魂以及前文提到的对本能的尊重令他不得不寻找更具身体性的创作手法。「《雍◎和》确实是在大架构确定之下,基于数百个加工好的声音采样片段,夜晚喝着酒,在房间里半即兴而成的。」
不过酒精的作用始终有限。在个人电脑全面普及的年代,电子原音音乐和声音艺术的创作与表演都几乎成了腰椎和颈椎的敌人。在YMO和Jean Michel Jarre现场影像中看到的音乐家要移动脚步并动用手臂、颈部和腰部去操作比自己还高的合成器,但当乐器被化约为一台笔记本电脑后,真的需要动的几乎就只有前臂和手指了。这对于一位满脑子想法的足球少年和吉他少年的束缚想必难以承受。「其实那会儿身体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卸下来了,」张安定说。「我记得我们在广州讨论过笔记本演出中身体的丧失。对我来说,这种丧失是非常真切的。不那么即兴肆意,又缺乏演奏性、表演性。可能是某种与舞台有关的场域的丧失。」这种丧失为他带来的是长达五年的创作空档。二〇〇八年,他全身心投入自己创办的咨询公司青年志,研究年轻人文化。然后到了二〇一三年,「憋不住了,厌烦了公司和商业的事情。开始琢磨新的可能。」
日本噪音艺术巨擘秋田昌美(Merzbow)在一九九二年的《Noise War》一书中指出超大音量与身体性是日本噪音相对于欧美噪音的特点。不过,类似早期非常阶段包含呕吐的戏剧性舞台表演或是Masonna的痉挛式跑跳这样的身体性并非张安定的目标。一来他在复旦时期的吉他即兴实验已经多少让他「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二来他在智性方面的求索也需要更复杂暧昧的形态方能满足。他给出的答案是「声响剧场」。在二零一四年的「中国声音大展——香港站」以及二零一五年于深圳OCAT举办的「声音分裂:声响语境异化」展览上,张安定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尝试把剧场感性带入声音艺术表演。他为声音分裂展所作的声响剧场装置与现场表演包含他本人的文本朗诵,以及采录得来的日常问答,与先前的电子原音作品大相径庭。对于素人听众,这些演出可以作为诗歌朗诵来欣赏。而对于熟悉前卫音乐语境的人,它又像是在问「为什么声音艺术家不可以直接原汁呈现前现代的聆听对象」,为什么采样和调变的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非乐音、噪音、日常音。我们确实有必要问问应该怎么听这些作品。是听它的文本内容?还是把文本念白当作无意义的声响去听(这对于普通话母语者不可能)?
在此,我们确实可以将他和Merzbow这位同样两条腿走路的艺术家作一对比。秋田的唱片与书籍产量都相当惊人。作为作家,他的课题主要是亚文化、民俗、虐恋、以及色情史。可以说,生于一九五六年的他是六零、七零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传承者。他的唱片与文本书写,和Kurt Schwitters的Merz一样,都是对既有社会结构中的杂碎垃圾的复权。但Merzbow很少直接为其声音作品构建详尽的文本概念框架,更多是通过标题或简短的文字说明给出暗示。若他偶尔在作品中使用人声念白,注重的也往往是其声响趣味而非文本内容,是能指而非所指。相反,张安定很愿意给自己的声音作品设计充分而具体的文本叙事。他的每一个声响剧场项目都始自田野调查和研究,并写有非常完整的施行计划。显然,这种工作方法令受过学术训练的他感到愉快和安全。但是,一个试图通过音乐创作从商业分析中抽离的人,必定不会满足于提问——规划——执行这一链条本身带来的快感。在心智与身体的搏斗中,身体再一次准备反噬。这也是为什么张安定的声响剧场阶段并没有维持很久。「很快我就觉得应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智性上、身体上,好像都感觉到了边界。直觉告诉我,可以停了。」那是二〇一六年。
您手中拿到的这个四碟套装《大平原:四个时刻》,就是他在后声响剧场时期的阶段性总结。它包含一八年的《亚伯拉罕的机器》与《荒舟》,以及次年的《不完全契约》和《剧场契约》。这些是与《雍◎和》以及声响剧场迥异的作品。它们融合了前文所述的两种倾向——对于直觉、本能和身体性的尊重,以及理念层面的思考与建构,可以说是张安定艺术生涯中期的总结与集大成者。
张安定本人为这一时期划出了非常清晰的界线,甚至会做出「一六年秋天,我决定开始重新做音乐」这样的判断。这不仅是对于早年乐队经验的回归,更是对实验的告别。他坦承这四张作品并无实验性,反而接近于某种浪漫主义传统。或许在电子原音阶段和声响剧场阶段之后,他再一次「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声响剧场阶段后感受到的边界让他选择了向后看。「脱离乐队之后很多年,其实我就没再做过音乐。我想试试回到单纯的音乐上来,回到简单的舞台。我想去演出,想让身体更彻底一点。智性减低一点。因此最开始试了试硬件,也做了现场演出,感觉还不错,就是效率相对较低。之后还是回到了电脑和DAW(按:数字音乐工作站)。」
把大平原系列当作纯粹的音乐听,应该是作曲家本人最乐见的听法。不用管大平原是什么意思,不用尝试去深挖《不完全契约》里「苦兽录」「碎士歌」一类的标题与音乐的关系,也不必去搜寻《剧场契约》里种种政治性人声采样的源头。妳大可以假装外国人,把这些标题视为autechre风格的无意义字串(「VL AL 5」「P.:NTIL」),直接享受这些暗黑的、苦涩的、笨拙的、欲求不得的、势如破竹的怪诞舞曲。不过张安定旧习难改。始终,社会学的思考和多年入世的商业咨询工作令他无法真的架空所有声响。「我做东西的套路是基于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本科时我虽然不怎么读书,都在玩乐队,但毕竟学校还是有(西方意义上的)左派氛围。我们读政治哲学,读马克思,异化理论。」这样的思维背景令他不可能对当下这一旧秩序瓦解重组的时代视若无睹。在二零一七年与青年志的同事们共同书写的一本书里,张安定提出了「大平原」的概念。仿佛一座雄伟的城堡逐渐坍塌,过去的层级关系消失、社交关系被重新定义、组织结构要翻新设计,所有人都汇聚在平原上,应对着貌似无限的机会与令人不安的未知。在这四张最初发表于上海数字出版厂牌playrec的专辑里,张安定试图用宗教和社会学意象(契约)召唤一个新世界。
尽管有这样的现实框架,艺术家本人也为这些音乐写了相当细致具体的文字说明,我们依然不该把它们视为观念作品。《雍◎和》作为一个句号让张安定看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哲学在声音创作上的限度。「我受福柯影响比较大,聆听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自我的方式。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手法对于声音创作的指导意义不太大。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声音就是政治的结果:哪里大声,哪里小声。听得见什么,听不见什么。声音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提出批判,但这种批判很难导向建设。」这是古老的追问:艺术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有效介入社会?目前看来,至少张安定对于那种声音地理式的调研与介入表现出了倦意:若艺术家的本能与直觉是第一性的,用声音试图政治性地介入现实就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大平原系列可以说是对古典(也就是他说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回归。一方面如前所述,文本和声音的关系不再交融,观念性成了一种假象;另一方面,它们也代表张安定正在逐步从静态、拼贴式的电子原音创作回到了演奏性的实践。如他为《不完全契约》所写的说明:「这八首曲子,基本都是二零一八年冬日,我在白天繁忙工作之后,断断续续十多个疲倦夜晚中的即兴……它是步履混乱,絮叨矛盾的。它是手工敲打,摇摆不定的……」如果要我进一步坐实张安定所谓的浪漫主义传统的话,我想说这些音乐在一种间接暧昧的层面上确实点了题。苦兽、顿足、哀歌、暗咏、Face Is The Mask Of Human Being、Revolution Is As Cheap As Louis Vuitton……这些标题或许不能直接对应到音乐,但却是过于直接地对应到了如今人们熟知的现实。张安定大口吞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的空气,用五脏六腑将它化为音乐,那必定不会是光明通透、爽快舒畅的声响和节奏。这是最诚实的音乐,是一个想做单纯音乐、数次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单纯音乐、而终究没能单纯的人留下的实录。我在其中听到的唯一次救赎,来自《不完全契约》中的最后一曲「骨舞录」。中段在背景突然响起的悸动,拥有穿透心魄的锋利。
纵观张安定十多年的创作历程,身体与心智之间的张力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在近两年与音乐人、画家和鼓手刘㔻合作的专辑《念完这首秩序的诗》里,可以听出他在有意为自己的音乐设下某些限制,订立一些规则。回看我和他在二〇〇五年的对话,我依然不觉得单纯靠听觉本能驱动的聆听可以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近年ASMR的兴起,恰恰就是声音聆听庶民化之后的结果。那种聆听或许简单而快乐,但不可能具备超越性。另一方面,二〇二二年上海封城惨剧中流出的电话录音获得了无数听众,这种与文本所指密不可分的聆听又何尝不是民众自发的一种偷窥式式美学(voyeurism)?在这样的语境下,艺术家把话筒指向隐秘和废弃的空间,或是通过调变和剪切拼贴声音以达到置换真实,拆解真实的目的,都已经无法再构成有效的批判。但我想张安定已经对下一步做好了打算。目前他正在研究早年电子音乐先驱如Stockhausen等人的技法,准备创作一件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现在其实是在继续学习,重新看了些关于实验音乐历史、二十世纪音乐史、电子音乐史的书。最近看了G Douglas Barrett的《After Sound: Toward a Critical Music》,我大致明白了自己其实一直想做的是什么。接下来希望能成为一名真正的composer(作曲家)。」疫情之作必定会用到其间流出的种种音声素材,至于如何使用和呈现它们,恐怕张安定本人也无法预测。但我确定,它一定会让难以安定的他,为身体与心智之间的钟摆找到一个前所未至的落点。
(如无特地注明,文中张安定引语均来自作者二〇二二年对他的采访。)
2022.04.04
2022 “丢失的日记”项目 – 作品设定笔记
一)关键问题:在科技加速生成的虚拟世界,听觉正在如何演进和塑造?我们以怎样的“人”的状态,重新聆听世界和面对自我?
在真实世界,声音作为生命体验和存在的重要部分,从出生到死亡,通过各种仪式,声音介入到人和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听觉文化是人们敞开自我,联结身体-自然-人造物,联结情感-意义-符号,通过聆听达到某种整体性/丰富性/联结性的重要方式。
随着技术发展,图像和视觉的中心化垄断了我们与世界交往的方式,人们的聆听能力在下降。虚拟世界通过完整的模拟和再造现实世界,实现了视觉景观的超级繁殖,人类感官的扩张。但是在其中,听觉又是怎样不断演进?声音环境被简化,丰富和有机性大大减弱了,意义丧失,这会如何影响人的自我感知和判断?新技术是否带来声音聆听和生产的新可能性?虚拟世界的听觉文化现在发展到怎样的状态?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生命体验?
在虚拟世界中,听觉对人们意味着什么?数字化/后人类状态的我们,如何用声音面对世界和自我的每一天?数字主体的感知是如何被重新建立的?有没有带来新的可能性?
二)创作概念:The Lost Journal 丢失的日记
1) 内容概览
这是一个丢失的笔记,一个人类学家田野笔记。这个笔记整理记载了虚拟世界物种如何重新塑造和应用声音巫术/仪式,来面对自我和世界。它是关于虚拟世界,声音和自我和世界之间关系的新叙事。它详细记录了具体的声音,物件,话语,环境,传说等细节,以及记录者自己的想法(以诗句的形式)。它是富有情感的,也是理性的。经过解码编码,人类学家拆解其中的意义之网,理解人们的观念和行动,观察和重塑声音与世界和自我的关系。
数字虚拟世界的一切,经由我们切身进入,展开新的聆听和审视 (声音和视觉的重构)实践,得以唤醒,得以重塑,去除掉自我与世界对立的二元。我们不需要一个复制现实世界,景观繁殖,充满交易和有用,高速喧嚣的虚拟世界。我们也不需要一个拥挤的充满看似新奇魔幻,其实仍然是现实世界象征脱胎的幻想世界。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世界,它既在又不在现实世界,处于临界和过渡。它不是现实世界的表征或象征性的投射。荒芜开阔,缓慢稀松,边缘零碎,恍惚游离,人与非人,万物有灵,静默诗意。我们的自我,和这样的数字世界纠缠在一起。人作为数字物种,可以重生。我们不是面对数字世界的沉思者,而是在日常实践/田野的关系语境下发现隐藏的意义。我们在一个新的世界中无能为力,什么都不做,游荡等待。世界溶解在自我之中的本真状态,世界荒凉之中所体验的孤独与存在样态。
丢失的日记,是我们抵达失去的,或者仍未实现的虚拟世界的一种尝试。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有机会重新探讨空间,边界,声音,主体,生死,劳作,自然,物体等等。就声音而言,个体与所在世界的感知与建构中,声音通常与感知空间,感知外部世界,交流,情感和记忆,私密性,文化性等密切相关,也呈现为声音场景/情境/景观。 数字世界的声响,应该具有全新的特质,呈现为新的声音景观。虚拟世界有自己的声音历史,也就是声音建构历史。虚拟世界的声音,应该是全新的世界,声音不是通过空气的震动,而是可以创造全新的音景soundscape。
2)组织方式
1. 法本手记:整个声音和影像,像是一个有不同章节的虚拟世界声音巫术的法本。如同翻开一本长长的卷轴日记。既沉浸在其中,又比较抽离的,静观我们如何在虚拟世界中生存。
2. 仪式历程:浏览这个法本,相当于经历了一场新的声音萨满仪式,通过声音与世界和自我联结,从而化身为新的数字物种,获得某种在新世界生存和审视的能力。把人在虚拟世界的声音体验,整理幻化和重新想象为某种声响巫术的完整历程。凝视的同时也被包裹。
3) 内容构成
1. 总体数据库:内容本身构成某种虚拟世界相关的特定数据库。数据之间关联,结构和呈现是关键。这些数据,无论声音和影像和文本,都会调用和混合使用。包括过去的历史中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也包括虚拟世界,真实世界,以及文化关联的。
2. 复调叙事: 视觉,声音,文本,各自构成三个独立完整的脚本。在每一幕上,又相互咬合,纵向成为一个完整的局部。声音,视觉和文本之间不存在一一语义对应的关系,相互错开,不同的叙事,增加相互的空间和可能性。
3. 文本内容:主要是第一人称叙述,观察者自问者的言语,半评论半虚构半提问。诗歌化的人类学田野笔记。短小的诗句,甚至词汇。不是字幕,没有画外音。穿插在黑幕以及视觉镜头中间。
4. 声音内容:主要重塑虚拟世界新的仪式化的聆听体验。从数字母体世界和空间中的内部聆听,到进入到外部开放世界大空间的聆听,再到所有生物之间的相互聆听,对物件的倾听,对自身身体的聆听,最后回归数字不朽的死寂聆听。包含虚拟世界的典型声响录音以及现实世界声响采样,以及融合部分音乐创作。里面包含了声音事件,声音物件。基于线上线下田野采样,电子原音和音乐的三层结构,围绕巫术建立的声音体验。真实世界的声音和视觉,扮演了桥接/调用记忆和传统的作用。
5. 视觉内容:主要拆解和呈现既在又不在这个世界的四个维度。包含从声音维度拆解,相关联的虚拟世界典型物件,空间,环境,人物,文字等,也混合了现实世界的真实视觉,最终所融合的产物。影像素材以静态图像,以及基于静态影像的后期动态为主,不采用录像素材。真实世界的声音和视觉,扮演了桥接/调用记忆和传统的作用。
5)风格描述
1. 风景化:整体是对虚拟世界的解构和重组,是对永不死亡的过度繁殖景观的一种抽取。因此具有风景一般的静态抽象冷静感,但也具有风景一般的广阔性和情感。
2. 运动感:充分利用5.1声道所带来的声音的运动感,沉浸感,带动视觉的运动。视觉影像部分,依据不同章节,建立自身不同的运动规则。
3. 仪式感:是建立在荒芜开阔之上的,不是过渡热闹的。
三)视觉部分的创作
1)第一幕 荒野母体: 母体生成/多重天地 (在世界中诞生的仪式): 多重世界。显现闪现,自我与世界在同一个母体生成。
1.点线面数:从几何要素中诞生的世界,渲染。沉默的电流之声。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空间开启的关键元素。渲染即生成。在渲染之前,世界蛰伏在抽象的几何母体里。我们看到数字世界混沌太初的状态。这些要素就是世界的缝隙,虚拟世界的基本构成/秘密。总在某些时刻向我们显露,让我们看到生成的过程。我们不断瞥见这个世界的真相,母体构成的基本面。
2.天地生成:生成多重世界,空间。多样性。在几何的抽象闪现之中,画面逐步稳定拉开,天地自然开始呈现。沙漠,陆地,地面,山麓,海洋,天空,云彩,光线。世界以不规则的单片几何形状,大片的单色构成,薄薄的一层,辗转腾挪,相互架构,演化成不同但似曾熟悉的空间。多个空间在平面之中展开,随时折叠,不再是单一世界。这些自然,不再是稳定单一的。
2)第二幕 裂出自然 : 风景间离/游荡碰撞 (与自然世界相遇的仪式):新的风景。游离的,碰撞的,闲置的,空旷的,真空的,非沉思的。
1. 风景/飞行:人和风景之间关系的重新设定。停在空中。没有人和其他生物,只有空旷,风声。上升下降,滞留空中。人平视风景,俯视风景,仰视风景,极远眺风景,超近观风景。风景以一种多种不同的角度和关系,被重新看待。在游荡和飞行中重新发现自然。这不是西方的写实风景,印象派风景,也不是中国山水意境。这是数字建构的新自然景观。它由人直接创造,又自由审视,它挪用现实世界,又无意中再造现实。它构建了一种混合的新自然性,在人造物和非人造物之间,在他者和非他者之间,在生成和完成之间,在清晰和混沌之间,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在神圣和俗性之间,在现实和梦境之间,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它有自身的新诗意,在与不在的诗意。 我们重新面对自然,理解自然,和自然形成新的关系。这种混合的新的自然性,指向新的意义,新的感受,新的象征性,新的空间性。我们不再简单崇拜自然,征服自然,或者与自然合一。我们自由的创造它,陌生它,靠近它,又离开它。总是在飞行中,看到,相遇。
2. 游荡/卡顿:我们在数字世界游荡和碰撞。有时候在无尽的空里不知所终。有时候在无尽的碰撞里卡住或者掉落。数字世界无边无际,但有边界。在世界的最远处,最深处,是真空,空的屏幕/材质,空的天空/海底/星空,不同颜色和质感的空,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层隔膜。各种各样的虚空,以图片或者动态小录像的形态。人就悬置在空的某处,不知所终。我们以身体和世界碰撞,以身体测试世界。碰撞各种边界,闯过看的见看不见的,世界的阻力。被建筑挡住,被边界挡住,卡住,停顿。静止。固执的重复碰壁。或者又不受任何阻力穿过。穿过大地,穿过建筑,穿过自然,穿过透明之物,穿过时间和广阔。
3)第三幕:捕食他者: 环顾聆听/模仿转化 (与他者交往的仪式):灵魂穿梭。人与非人,物与非物,模仿转化,创造与交换,相互凝视,经验与倾听,自然与本性。人处于中间状态。模仿保持同一和差异。
1. 环顾与聆听:在抽象和具象之间,意味着没有距离,没有对象,也就没有边界。动物,植物,人类,万物,山川河流,神灵。重新看,重新听。看物体,看他人,看自己,以各种视角,正面侧面反面,高处低处平行处,各种方式,远离身体的任意视角。无所谓凝视,一切都在流动和变化。听见生命,听到世界的反馈。在万物的内部。让物走向自身。相互凝视,经验与倾听。
2. 模仿与转化:人和动物相互进出取代各自的身体。万物有灵。人可以化为各种形式,非人类之人的降生,人和动物和其他物相互进出,取代各自的身体。模仿是一种存在方式,无法成为谁,也无法完全转化。在模仿之中,万物转化。相似又保持差异。灵魂穿梭。人与非人,物与非物,模仿转化,创造与交换。你通过模仿成为一颗植物,但你又并不完全是一颗植物,这种相似又有差异,保持了相互的沟通以及各自的边界。身体就是传输的介质,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其他之物。没有两分的执念。
4)第三幕:废墟时间。荒废静止/雾气不朽 (与时间相处的仪式):没有终结的存在。荒芜但永不消失。回到一个混沌的世界。一个重新模糊,彻底抽象的世界。生命陷入一种过渡和重生之前的状态。
1. 静止悬浮:停止劳作。停止舞蹈。战斗。社交。朝拜。交易。停止这一切。看着发呆的avatar,让时间就这样流逝。看着无人的岛屿。不动。
2. 雾气不朽:没有死亡。只有不断重生。永不腐烂/停滞,景观的不朽。废弃。雾气笼罩。迷雾中的抽象物件,抽象的世界。天空的尽头。
四)声音部分的创作
一个四幕的祭祀音乐。有自身的整体性。仪式化的,有宗教性的,有神秘性的,声响化有新鲜度的。音乐的有效使用,帮助声响变得沉浸和情绪化。
1) 第一幕 荒野母体:在母体的黑暗中,像是在梦中展开,闪现里见到世界。然后世界逐步打开,见到荒野。对数字母体空间的内部聆听。
1. 情绪上:母体的空间,黑暗,未知。瞥见世界隐秘的。
2. 声响上:用声音劈开世界,测量空间,理解空间。世界在沉默之中诞生。燃烧的声音,喊叫的声音,高中低频率分野。瞥见世界的隐秘,也召唤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
3. 结构上:是一个大场域的东西。长音扩展空间广度深度。还有声响类似黑暗中的闪电,从各个角落发出,测量空间,用声音进入世界。
2)第二幕 裂出自然:接触自然,自我和世界的新关系。非客体,非沉思,也非融合的。而是相互间离,碰撞游荡,非沉思性。对纠缠的新自然性的聆听。
1.情绪上:不能太沉思化,长音旋律等,要慎重。
2.声响上:不复制自然声响景观。描绘的是时刻纠缠但不断离开的状态,因此有自身的运动性。充分利用多声道,绕来绕去的风声,各处走动的脚步声,四处的碰撞声。
3.结构上:是核心是两条线的相互纠缠和时刻离开的过程。风声是一条主线,压抑黑暗的弦乐是另一条主线。其他采样在上面,不断插入。
3)第三幕 捕食他者:与他人之间自由的组合和交往。对流动的主体性的聆听。
1.情绪上:是自由的,流动的,没有恐惧的,轻盈的。去主体的。
2.声响上:有东西粘稠,破裂,碎片,重组,流动的质感。水声。长笛的轻盈。
3.结构上:主要是复调和声式的多声响面的流动和重组。复调式的,和声的。
4)第四幕 废墟时间:回到天空,面对荒芜,不生不死。对荒芜废弃的聆听。
1. 情绪上:宁静,氛围,但并不是美好。极简的停滞。
2. 声响上:留白,极简。使用不和谐音程的极简钢琴演奏。某些细碎的声响。比如树叶摇动的声音,昆虫窸窣的声音。
3. 结构上:点状的,留白的。稀松的。
2022.04.04
2022 “丢失的日记”项目 – 剧本
by Zafka (translated by 李如一)
第一幕 荒野母体 Wasteland Womb
我瞥见 谁 在母体的延展中 站立 / 以风声 替代呼吸 与休憩 / 任 世界把生成 显露 / 于缝隙 碎片和云泥 / 缓慢 而后加速 / 亲眼得见 自我 与世界 / 本是 残缺一体 / 往复 新生 /
有人 手持天地 / 时空 穿过弯曲的 足背 / 繁殖 穿梭 跳转 / 层峦叠嶂 围屋而猎 / 每一处坍塌 供奉一种世界 / 无人无神 / 荒野 不知疲倦 / 日夜降临
Whom do I glimpse standing in the sprawl of the womb / Trading breath and repose for the sound of wind / Letting the world reveal its generation / among cracks, fragments, cloud, and earth / Slowly at first / then accelerating / Witnessing self and the world / being a disintegrated whole / reboot and reborn /
People, holding sky and earth / Spacetime passing through their curved feet / They breed, shuttle, teleport / through and among strata of planes, hunting / Every collapse is the oblation for its own kind of world / Void of human or god / a restless wasteland / emerges everyday
第二幕 裂出自然 Nature from Fission
在 与不在之间 / 生成 与遗弃之间 / 他者 与非他者之间 / 记忆 与想象之间 / 谁 几乎杀死 自然 / 又从自然中 裂出 / 创造 而后陌生 / 相遇 而后远离 / 以新的风景 间离自我
直至 委身虚空 / 惯于奔跑 飞行 / 惯于 弃绝沉思 / 仅以身体 测量世界 / 碰撞 游荡 纠缠 / 固执的重复 亦或下坠 / 穿过时间和广阔 / 亦或静止 / 悬置万物 而出神
Between being and not being / generation and abandonment / the other and non-other / memory and imagination / Who almost killed nature / before breaking away from it / Create, then estrange / Encounter, then separate / Alienate one’s self with these new landscapes
Until lending oneself to the void / getting used to running and flying / getting used to ditching contemplation / and measure the world with only body / Clash, wander, entangle / Repeat stubbornly, or falling / through time and wilderness / or staying still / floating entranced with all beings
第三幕 捕食他者 Hunting Others
由此 心无挂碍 / 抹去阴影 与亲近的恐惧 / 仿佛贴身 听见 / 指尖裹住四野 极远吞噬极近 / 无内无外 似是非是 / 触摸过的 每一刻具体 / 从平滑的抽象中 涌出/ 顺势撑开 凝视的深渊
唯有 / 模仿 体察此刻的存在 / 即时转化 叠起名字与身份 / 似他 似我 / 灵魂似流水 不朽 / 随时成为谁 但未曾记得是谁 / 捕猎他者 蚕食自身 / 无他 无我 / 坦然负罪 浑然一体
From now on you are free / Wiping off shadow and the fear of intimacy / as if hearing close by / fingertips enveloping wilderness / the far end encroaching the vicinity / Inside and outside become one / what look alike remain different / All the moments of concreteness you’ve touched / swarm from the smooth abstraction / and push open the gazing abyss /
And you can’t help but / imitating and perceiving current existence / Transforming on the spot / layering names and identities / Like him, like me / The flowing souls don’t rot / they turn into someone else at will / but never remember who they are / hunting others, cannibalizing self / otherless, selfless / bearing the sin unperturbed / all things as one
第四幕 废墟时间 Ruin’s Time
该是谁 通达天地 / 在高处抛洒时间 如薄雾临空 不散 / 又把世界略过 归于平面 / 废弃劳作 藏于无人之地 / 徒手取来荒芜 这永不枯竭的收成 / 完好无损的 废墟里 / 有人 一再抵达
Who’s towering towards the sky / scattering time from above / like thin fog gathering / And who’s ignoring the world / folding it flat / Abandoning labour / hiding in the deserted land / With bare hands, they grab desolation—the eternal harvest / The intact ruins, witnessing / people arriving nonstop
2022.04.05
2022 ”露台“项目 – 作品设定笔记
一) 现状:作为城市的太原以及太原声响的多重性
1)三重太原城市:长历史时段的太原-2500年;经济失落中的太原-近20年; 城市再造中的太原-近10年
2)两重太原声响:非地方性声响的同质性——城市化进程; 地方性声响的消逝性——非遗与记忆
二)挑战:现状所带来的几个创作挑战
1)外来者:一个外来者,短暂的停留,是否以及如何进入太原?
2)景观化:如果大部分地方都在非地方化,那么去寻找地方的差异性声响/独特性声响,是否真的可以推动地方认同?还是说,更多是一种符号化的怀旧,景观化的审视,情感化的消费?(比如,新修的太原古县城,雇人表演,恢复了过往的各种叫卖声)
3)转换性:如果地方性的差异特点,往往存在于边缘和过去,历史和记忆,那这些独特性如何在当下被转换?
4)具身化:如何不把地方声响作为一个采样对象,一个景观对象,而是作为具体的可以进入的历史空间,生活空间,身体空间,那应该从哪里入手?声音可以做什么?艺术家可以做什么?
5)想象力:如何超越非地方性和狭义的地方性,藉由声音,通往具体生活世界和具体的情感,达成一种新的地方想象?
三)问题:地方与非地方张力下的“地方想象空间”如何可能 —— 新地方可能性的探讨
1)地方是与人相连的具体生活世界经验
2)地方是流变和未完成的
3)地方认同是多样化和动态化的
4)地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四)方法:新的田野思路与特定场域的田野地点选择
1)三个转变:从田野录音到田野呼吸;从城市聆听到地方想象;从大的城市到小的地方
2)三个问题:历史感问题——进入个体生命测度的具体历史;整体感问题——超越差异独特性的共同关切;能动性问题——撬动自我想象与社会想象。
3)一个聚焦:从抽象的太原,聚集到离自己最近的当地地方。田野围绕美术馆所在长江社区展开。美术馆所在的长江村,就是我所在的地方。讲到太原,也是我可能最终花时间最多的一个空间,一个最有可能建立关系,建立情感的地方。长江村,也是太原城市化近十年,所塑造的无数个具体的新地方之一。在这里,历史和现实的沉淀,得以具体的呈现。长江村背后,有围绕关于地方和社区营造的努力。从2015年至今,长江村作为地方,怎么样了?
五)田野定位:作为催化物的艺术家“私人地方想象”实践
1)私人化:“ 某种催化物可以将任何一个物质性的地点转化为一处地方。只要你愿意,任何一处环境都可以做到。这是一种深度体验的过程。一个地方是在整体环境中由情感创造出来的一个碎片”。私人所赋予意义和情感的具身生活体验,是地方性涌动的根源。在中国本土城市化的持续进程中,地方性仍然是流动变化和多元的。暂居者的地方体验,也是这涌动的地方性的一部分。 作为短暂停留的游荡者,也可以带入私人生活经验,记忆与身体实践,来赋予地方以自己的意义和情感。即使短暂,也能让一个空间成为某一个人的地方。而这种地方,也可以分享和联结到某些人。
2)分享化: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公共性的缺失,人们的私人地方经验,人与人之间的多元性地方,无法沟通达成某种共情。最后残留的地方认同,只能在物理地标等层面留存。因此,构建分享场域,分享给他人,启动对话,确实是重要的。这种分享也要保持批判性,有反思和想象。
六)田野工具:构建基于人文地理学的“地方音景田野观测表”
1)观测维度扩展:地名/命名体系 – 地理位置信息 – 空间特征 – 场所描述 – 声音特点 – 历史维度 – 身体维度 – 社会建构维度 – 关爱维度
七)田野规则:声音行动
1)田野呼吸:就是走走停停,听听看看。随意游荡进入各个边边角角。偶尔拍照,不做笔记,不录音。对整个地方,有了一个最简单的初步体认。放松。上天入地。自在。
2)田野观察:再次游荡。自然停留。简单拍照,初步笔记,偶尔录音。看到听到了更多具体细节的环境和人,具体的生活经验。开始有一些更具体的身体体验,以及地方想象。结束后有初步的具体地点list,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小地方。如果我住在这里,我会在意,以及停留的地方。
3)田野行动:重点游荡。停留时间更长了。录音和细致的笔记多一些。因为对这些地方的不断熟悉,可能是情绪所至,跟随现场声响的实时聆听,开始即兴做一些小的声音行为。我称之为“写一首声音的诗”。
八)作品构成
1)目标:超越狭义地方与普遍非地方性,生产“新地方性想象”。注入私人情感和意义,分享自己对当地社区和太原的私人地方想象,转换空间为地方,以地方想象来重建地方。
2)概念:露台。在美术馆四楼户外露台,构建一个有关长江村地方想象的地点。露台,是西方都市化生活方式发展中的一个符号。在中国,露台与戏曲舞台有关。在这里,环望仍在建设发展中太原长江村,我们问自己,“这是什么地方?”
3)作品一:“这是什么地方?”
1. 户外霓虹灯光装置:“这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提问,给自己,也给对面的社区居民,也给观众。需要考虑白天的样子,以及晚上的光照强度,光污染,以及关闭时间问题。要用艺术家手写体。
2. 户外声音装置:通过声音来转变地方,从同质化的空间里,寻找人的空间,通过转换当地声响环境,营造一个新的声音场域。结合现场户外已有声响,把露台当成一个新的地方/戏台,转换为具有想象力和启发性的新地方性声响环境。从日常环境声响中,抽取出抽象的声响,结合氛围音乐等手段,反向改变环境。户外已有声响,包括建筑工地声响 +社区遥远声响+街道车流声响 + 鸟鸣蝉鸣蟋蟀等。使用户外音箱,四只。覆盖露台的四个角落。
3. 户外音景观测文本:比较过去做声音日记的世界音景项目的记录监测方式,构建一种新地方性甄别和监测的体系,基于人文地理学的“地方音景田野观测表”,并呈现基于此的声音写作文本。艺术家作为暂居者,游荡者,选取具体地方,进行田野音景观测和协作。要包含地方性判断中的冲突,矛盾,现实以及想象力。
4)作品二&三:想象的风景I & II : 一种虚幻的,导游式的,多重地方性和历史嵌套的叙事。
1)想象的风景I:装置,在露台上做一个观望聆听台。防风。有长条窗口。远观,有封闭小剧场的感觉。有音箱,可以深度聆听。有人声旁白讲述。一个小型声响剧场叙事。讲述文本,混杂着传说,神话,历史,未来。呈现地方塑造的复杂性。声响和眼前的视觉形成差异。可以有声音的采样混杂其中。造成视觉和听觉的错开。看到的是高楼社区,但是听到的部分,声响的差异性,以及叙事的虚构性,会拉开距离,形成剧场感。
2)想象的风景 II:把短视频up主“街拍太原”小余的视频素材作为田野,再剪辑和创作。通过小余的个人行走,拍摄和讲述,把太原作为空间转化为自己的地方。每一个个体在空间的实践,就是对地方的想象,就是对地方的重构。太原作为地方其实包含了很多的褶皱,小哥看到了这些。从自然山野-城市遗迹-历史文化-废弃空间-建设拆迁-遗留老旧-新建小区-新城设施-城市景观。这是多重的太原。这是一个交叉结构,从一个差异化的自然与城市很大空间的两头,到中间最小的家空间这一个点。可以做一个交叉结构的行走,走过这些褶皱,把这些褶皱给重叠。两端行走到中间,家。
在剪辑原则上,要注意 A)去太原抽象化,这是具体太原的,但也是更多城市的。地名要去掉,抽象化。B)再造地方想象: 不是简单非地方的,遗弃的,而是被转换的,有诗意的。C)通过行走叙事:深入城市空间肌理,也就深入到历史。镜头的行走感,临场感,实地感,晃动感。D)五重文本结构:具象音乐一层,小哥导览声音一层,原有字幕一层,视频画面一层,现场环境一层。声音和画面错开。E)围绕风景展开:每段都是一种风景构图。想象的风景,糅杂的空间和历史。F)图像关系结构:图像之间的关系结构,如何运动,重构叙事。
3)作品四:回家的路(营造接入)
1)与美术馆工作人员,商量打开从美术馆到社区,回家的通道。
2022.04.03
2021 “露台”项目 – 这是什么地方?(声音写作文本)
鱼涌河岸 (037.5309 N, 112.3623 E)
东边有山。游过这长坡,就是最高的地方。从下往上呼吸,有九十米的垂直落差。安静走一个来回,需要十二分钟。气流旋转,徐而不疾。人或者物,就在离地半米的位置,适度的漂浮。我想,这里是空气稍薄,但让人安心的地方。
你是鱼类。北方往西,飞行六百公里到此地。遥望长坡。医院,学校,社区中心,售楼处,养老院,美术馆,家,渐次排开。人群行进。走路,快步,骑自行车,电动车,开小车,大卡车,有条不紊。不短的长坡,不宽的窄道。就这样,逆流而上顺流而奔,树木孱弱细碎作响。东山晴在高处,巨大而闪耀。长坡犹如一根脐带,就这样挂着。
我习惯侧身,坐在学校门口的水泥障碍墩子,看鱼来鱼往,听声去声来。横穿马路的排水沟铁板栅栏,如同人的腰骨(一些坚硬的耗损品),被过往车辆持续施压。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一分钟,两下,四下,十六下,三十二下。声音是卦象,概率的游戏,聆听之后求得的万种可能。这长坡,有自己不确定的节奏。
长坡中段趴着一座短桥,常有鱼群拥堵。三天时间,两次发呆,七十八分钟。这是当地最佳的出神之所。鱼群在头顶跃过,脚底穿行,被甩开,又冲上来。藤蔓涌向河岸,藤蔓又爬上桥头。一侧的桥栏坏掉了,生在一起的灌木也坏掉了。大把裸露的电缆穿过藤蔓遮住了桥栏扶手。他们和植物长在一起,缠住桥两头的小店。我在电缆上画下一道符咒,许诺草木青绿,灯火延绵。我在桥头旋转双耳,放任河流经过身体,声音趟过器官。
只要爬上长坡,总会有人背身离去。重庆小馆厨房轰鸣,油烟喷射在售楼处飘来的古典音乐里,掺杂着一旁养老院的宁静。有女人无声掉眼泪,甩开呆滞的中年男人,径直下坡。如果你经过这长坡,别忘了找到饭馆墙外那块有些粘手的天蓝色金属板,再多划上一道印记。
我就这样一路上坡。以身体持续碰撞这长坡的两岸,跟随声音触摸万物,用笔随手记录空气波动的线条。我把它留在沿街的墙体外侧,留在建筑工地的绿色防护网上。我还遇到过一个白色的“向”字。如果你恰巧撞见它,请在它一横一竖的字体泡沫板上,用铅笔再次写下祈使的诗句:“向这长长的坡道,砸下一顿的缓慢与憧憬。”
白马夜行(037.5303 N,112.3638 E)
这里属于夜晚。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这是游荡者的腹部。第一天傍晚,我发现了这里。
这是一座桥。顺着山势,欲望悄无声息的滑溜下来,不知道会通往哪里。向左回旋的曲线,一眼望不到头。就这样持续下坠,就这样悬挂向左,在空中带着尾音。我在山谷,社区地势的低处,抬头望远,东山晴在最高处。
这是一截阑尾。在社区的下腹部闲置。桥上少有车经过,也少有人经过。空空荡荡,偶有山风。山脚沉到桥墩之下,摊开了修车厂,停车厂,一些闲散的机械。目光顺着山腰爬升,灌木丛和野生植物开始塞满山坡,密不透风。瘦弱的手机信号塔高耸,能听到云里传来的轻声嘶鸣。回头张望,远处高速公路隧道口的自动监控车牌拍摄灯,在黑暗中孤寂眨眼。
继续顺着桥慢行。你会遇见夜行的父女,孤独的夜跑者,寂寥的机械驾驶员。呼吸,呼吸,呼吸。在这座桥上,有机生命和机械物件,几乎是同样的心跳速率。声音如同水墨滑过宣纸。远远着力,由浓入淡,温和的冲刷到你眼前,又迅速消逝。每一个声音,都如同这大桥的曲线,向左远远滑过。呼吸,间歇,呼吸。一个,一个,又一个。中间有无需计数的沉默,足够的留白,没有丝毫局促。
这是生命松弛之地。空旷与开阔之上的人造建筑物,才是此间的主人。我在夜晚,执意敲打金属的桥杆。手感生涩,笨拙。但真切踏实,自觉恰到好处。手掌每贴近一次弧形管,身体就在风里扩散一次。几百米长的栏杆,击节而歌。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叮叮叮叮。把黑夜震开一裂缝,在山谷里划开一刀水流。这是一只巨大的铁鸟,卧在山谷,细声鸣叫。这是一匹踌躇的白马,扭头而行,轻声震蹄。这是一处光滑的背脊,附身峭立,传递爱意。
就这样在空旷里闲置。我是游荡的过客。夜晚的白马,在山谷一路向南。只有不间歇的敲打,触及一处具体的材质,激活一座具体的桥,感受一种具体的建筑,我才能接近你,接入此地,接通周遭的城市。
第二天深夜,我再次发现了这里。你好啊,游荡者的腹部。
锦猫歇停(037.5309 N, 112.3635 E)
我在午后抵达。这是一处丁字街口。一侧街道的最高点,顶在另一侧街道的腰线。要往哪儿去?东山晴就在街口。远处东山看起来颇为真切,伸手只有几丈的距离。街对面学校工地的工程吊车高耸,单脚鹤立走在群山之前。再往高处走,是家具厂,太原解放纪念碑,烈士陵园,苍松翠柏,还有一个怯生生的驾校。
这个街口,有种叫人莫名静默的悬停感。一根有弹性的钢丝,在白净的空气中拉直紧绷,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只是持续微微上下抖动。据说很久以前,这里站着一只身形巨大的猫。它回望东山,警觉轻巧的同时抬起左前脚和右后脚,但尚未来得及落下,就在回首瞬间,被山神定格在路口,再也难以挪动脚步。
这是悬置之地,停滞未决的空间。此刻,头顶树上的蝉是单数的,呲呲鸣响,听起来薄薄一层,没什么颜色。来往车辆习惯了形单影只,习惯了下坡前呼吸的一口空白,上坡后的一个停留发呆。在这个地方,给人打开了一个间歇,不加判断的真空。
我还卡在街口,不愿走动。马路对面,工人们在路边小店吃大碗的刀削面,抽烟聊天。店门口女人用力洗着拖把,男人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小心翼翼上车,女儿在一旁来回蹦跳消耗自己。卡车司机也歇息了,三三两两蹲在路口弯道处树荫下,扑克啤酒香烟零食,堆了一地。整个街口,除了混凝土罐大卡车偶尔有些粗鲁,电动出租车和小电驴异常安静。至于驾校的新手们,早在距离路口五十米外,悄无声息掉头往回开走。
只要是活动的,都减速停歇了。都说在这个街口,如果你学会气流转换之术,把许愿的信息融入一直想要的气流,可以在悬停之间获得新生。但气流在哪里?应该在物体引发的波动之中吧。那又该如何触发,改变,或者加入这种波动呢?
我决定与植物沟通,转换这个地方的气流。在街角找到喜欢的一颗树,轻触树皮纹理,细致了解树叶形状,决定下笔的轻重。听着街口的风,我用黑色水笔,在树叶表皮上写一些此刻的信息给你。“粘稠转向,撕开了航道”,“滑行至深渊前,请保持左舵”。但愿吧,敏感的植物会感受一些指尖的震动,就此劈开气流,改变航道。
云雀剪雨(037.5307 N,112.3634 E)
不下雨时,这个地方算不上一个好地方。下雨时,这个地方,才能显现出空间中的隐藏结构。就像南方的山林,只有在雨天才能知晓,林地之间防风遮雨的缝隙,真是天赐的。人和万物都潮湿起来,除了纳入这空隙的片刻身心。
长盛苑小区就在东山晴马路对面,至少有20年的历史。楼层不高,楼距适中。喝的水,还是地下一千五百米的井水。小区一侧临街,一侧靠坡。临街的房屋出租,开成了杂货铺,饭店和诊所。靠坡的地方不小,一大半变成了菜地。满地的瓜果蔬菜,熟透了就一路滚落到山脚。
跟着居民溜进了小区。到处是旧物。沙发,衣服,拖把,篮球,板凳,零散躺了一地。阳台的防盗窗内,植物花卉,锅碗瓢盆,杂物用品,堆砌成林。生活简单赤裸,就这样稀稀拉拉,遗落在楼宇之间。这段时间结婚的新人不少。总有伴娘站在单元楼梯的门口打电话,楼顶拉扯下来的彩旗带子快要落到她高耸的发髻上。她脚下的下水道井盖,贴有去晦保平安的大红纸条。她的身侧,男孩偏着头蹲在破板凳上看书,老人扶着楼门发呆望向空地。穿湖人队球衣的少年踢开旧拖把,默不作声跟着妈妈回家。
仿佛掉进了静止的旧时写生图。有人从生活的岩层中,毫不费力的拉扯出一段日常切片。可这切片的秘密,留在了社区的孔洞之中。下雨时,小区水泥地面积水发亮。在五号楼的东北墙根,不多不少,有一块只够单人坐立的干净地面,滴水未沾。那正是孔洞的所在。只有在足够狭小的孔洞里,我们才能容得下眼下稀松的日常,被遗忘的记忆,还有些许暗淡的未来。
我在的那天,刚好赶上午后阵雨,偶遇了孔洞的开启。转身躲进洞里,贴着墙根听雨,声音如雾气笼罩,漫山遍野。泛起的墙皮上,全都是雨滴聚集和下落的影子。我看见屋顶上方的云雀,正在舔舐空气的湿度,穿梭于雨滴间的真空,用尾翼剪裁云彩。顺着云雀飞行轨迹,我把墙皮上雨水投影之间的空隙,用铅笔忽深忽浅的涂满。你看,在社区墙根上画一幅山水,可以联结地面与云端,物件与灰影,现实与幻想。
就这样,藉由雨水,我独自一人跳进孔洞,又如云雀般,改变气象与心境。在这雨后的图景里,存有一些暂时的提问,和即将失效的答案。
鲸跃边界(037.5320 N, 112.3623 E)
在黄昏前,尾随一群孩子,你就能找到这里。准确说,这不是一个地方。这里是边界。为了保护和区隔地方,人们建立边界。边界,在两个地方之间,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
东山晴顺着坡势建楼。社区西侧,两期楼盘的中间,有一道半人高的白墙,蜿蜒数百米。站在一侧望过去,边界外的楼盘,仿似水中冒出来的荷花,只看得到半截生命。而在这侧楼层空地上停满的汽车,因为地势较高,阳光照耀之下,金属车皮闪亮,折射出远方风景。看起来,有种即将开往天际,穿越远处高楼的虚幻感。
孩子们顺着边界玩耍追逐。他们每天都要巡边。对他们来说,边界比其他地方重要得多。边界线并不是一条单薄的线,而是沙土,石块,野草,昆虫,玩具和垃圾。边界墙并不是空白,而是污渍,泥点,破损,缺口和划痕。边界是隐藏的历史,未知的世界。边界也是私人领地,身份模糊的公共空间。
如果你跟得上,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巡边。随风聆听空气的流动,你会发现,声音并没有边界。孩子们尖叫,推动边界往前滚动,声音一路顺势跌落。一声尖叫,足以轻松穿过边界,击碎对面高楼的窗户玻璃。玻璃掉落的回响,在边界之间来回震荡。实际上,人们早已习惯了在边界两侧对望,聊天说话。话语借着风飘来飘去。如同口袋里的钱币,总是不经意间失而复得,好像从未丢失。
我在边界远眺,黄昏的阳光依然灼眼。蹲下来,跟随声音在阳光中跳动的阴影变幻,我把墙上的柏油污渍,水泥残点,联结勾勒成星空中未知的星座。边界上空隐藏的鲸鱼被唤醒,身形笼罩了整个空间。空气,泥土,海洋和飓风抬升起来,瞬间淹没了边界。边界哪里都不在,就在其中。边界不是结束,只是这个地方的重新开始。
如果你路过边界,可以稍停片刻,在长长的边界墙上,添加一个未知的星座。毕竟在月夜,它们会集体跃空,召唤打盹儿的鲸鱼,占领高楼与天空之间的空地,重新联结你我,再次宣告,边界之外,并无地方。
大象俯首(037.5312 N, 112.3631 E)
找个地方,坐下去。屁股直接落到地面,跳过凳子椅子。没有隔阂,人就踏实了。抵达这个地方的唯一方法,就是无所顾虑的坐下去。是否得体,是否干净,是否舒适,都不在考虑范围。真正紧要的,是身体移动与环境碰撞,找到空气和身体感知交合的舒适点作为入口,顺着气流就势坐低。
整个院子声音松散,人群下沉,长满了各式颜色和形状的蘑菇。在东山晴,傍晚到深夜,楼群之间的公共区域,人群流动,自然聚集成堆。妈妈们带着幼童,顺着低低的路沿成群围坐。她们和孩子有同样的高度。送快递的小哥,累了蹲在路边,打开手机看短视频,抽烟休憩。他和妈妈们有同样的高度。
我喜欢傍晚在院子里游荡,跟随人们随意移动。他们在哪里坐下,我就坐在哪里。低低的路沿,切割了风景,划定了水位线。沉入水面,这是另一个地方。幼童蹒跚学步,不稳定的身体嘎嘎晃动。围着空地绕圈康复的中风老人,脚底摩擦地面,压注了全身的重量。男孩胯下急切的自行车,拖着橡胶车轮压过水花,把尖叫甩了过来。眼前还有两只甲虫在过马路,梭梭作响。如果沉得再低一点,草叶摩擦声也开始变得清晰刺耳。
社区楼宇间的地方,是身体自行选择和界定的实在空间。道路,路沿,树荫,座椅,设施被提前规划固定好。每个人的身体感受和人群之间的群落气息,却得以保持变动不居。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我说不好。我就坐在一块灰色的石头上。你也许看不到我。但我只要抬头,就能瞧见你。
这是地表的低语。声音在低处,要贴近地面才听得到。身体比我想象的自由。这是一场即兴的身体芭蕾。笨拙如大象,灵敏如大象。我要做的,就是顺从身体,贴近地表,持续移动。在任何一个身体感到地球引力的地方,没有顾虑,没有遮掩的沉入地面。
等你下次来这里时,记得找个路沿坐下去。起身时,随手拿块石子,划一个几何记号。可以是三角形,圆形,或者简单的长方形。这是一个邀请,邀请一个陌生人进入另一个空间的邀请。这个空间里,有另一个地方的存在。
鸣虫扩疆(037.5312 N,112.3630 E)
如果错过黑夜,我不会遇到这么有趣的地方。那会儿,夜幕早已降临。整日游荡,疲倦之中,我有些失去了方向。我停下来立住,就像一棵树,任凭风吹,顺着枝丫作响,想着最终总会得到指引。站立的三十分钟并不漫长,甚至有些享受。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应该是恰巧遇到了只在夜里闪现的某个地方。
这里大概是东山晴社区其中一幢大楼的拐角处。黑夜里我看的并不真切。草丛和灌木围住了建筑的边缘,好像在黑色的海浪上,包裹上了一层浓密的毛发。看似柔软,但深不见底。虫鸣持续不断,几乎遍布了所有视野所不能见的暗黑区域。我也不确定,听到的是哪几十种昆虫,又有总计多少只虫子在合唱。
虫鸣的节奏,有一种极简主义的传统,带有节奏复杂的精妙变化,不断叠加生长。跟随虫鸣之声,大楼拐角处的小小站立点,伸缩自如往外扩展,犹如涨潮蚕食海岸的海浪。包括我在内的身边万物,只不过是声波持续冲刷之下,随波逐流的普通物件而已。
重要的是,搭乘声波旅行,我所能感受到的空间不断往外延展。我听到游乐场的孩子被虫鸣驱赶回家。健身女子的身体跟不上虫鸣节奏被迫呼呼作响。楼门口聊天的老男人们被虫鸣压制,气息低弱。我越过建筑工地,抵达了几公里外的山野,听到了动物的嘶吼。虫鸣之下,狗屎发白,野菊花枝叶残破,弯曲的钢筋从水泥块里冒出头来。
这是可以伸缩的地方。虫鸣就是空间。声音把人和物,都染上了金属的质感,发亮的颜色。声音不在空间之内。我们在声音里殖民,开拓空间,定义地方。我未曾困惑于人类的喋喋不休,却难以理解不间断的虫鸣。在这个地方,我开始尝试弃绝语言。那就用舌尖抵紧牙关,提升频率,尽力发声,努力成为虫鸣的一部分。声音从口腔开始,延续到整个躯体,嗡嗡作响,又逐渐融合进入外部空间,美妙至极。是啊,声音从来都是空间,自成一方。
其实,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些静默和耐心。静静的矗立,跟植物一起听鸣虫,和声音在一起,把其他看成边缘。忘记身体和大脑,忘记目标和方向,忘记差异和疆域。就这样站着,在鸣虫的宇宙地方,跟随虫鸣四处飘走。无论在哪里,我总会再次遇见你。
山鹿隐角(037.5308 N, 112.3629 E)
人疲劳时,适合放低身心,寻找水平面以下的藏身处休憩。下午四点,一路歪歪斜斜,直到快撑不住,我才找到入口。这里罕有人至。在机械的领地,人的干扰值被压缩到最小,虚空的宁静指数上升到最大。
因为顺山而建,东山晴高层住宅的车库,可以从山脚小区内马路一侧入口,直接开进来。车辆排着队,从巨人的脚踝处侧滑而入。这个高度恰到好处,既在地表之下,又保留了接触阳光与现实的通道,并没有感觉到潮湿阴冷。
准确说,地下车库并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人在乎人。车库的地面材料有一种粘稠质感。车辆进入,都市生活的底噪与粗糙,被顺势黏住剥离,连人带车,只剩下光溜溜无害的内层。把车交给车库,人从最近通道迅速离开,逃离到地面。向内的抽吸力,制造出一整片肃静的真空。这让我想起来,我去过不少无法分辨方向的高原,那里空气稀薄,行动迟缓,让人内心安宁。是啊,只有难以生存,少人的地方,才会给人留有足够宽广的,关于人的空间。
我开始走动,漫无目的。我敢肯定的是,这地下高原里藏了几只山鹿,行踪不定。我去的时候,它们出现在南边入口处,北边第三根梁柱后,以及西边第二根梁柱上方屋顶钢结构的顶部。我顺着鹿角找到它们。其实过程并不容易,需要一些运气。山鹿的鹿角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固定形状。它们依据自身对地下空间的具体感知,实时变化,随意生长。有时,鹿角布满整个车库。有时,鹿角细如微尘。山鹿并不是空间的守护者,而是空间的另一种有机生命形态。
因此,我们更需要耐心细致聆听与等待。每一只山鹿的鹿角,都会无休无止的击打地面和梁柱,发射特定频率的声响,以特定的节奏,持续的变化。极短的“滴”,每九秒一次。连声的“哒-哒”,每五秒一次。长音的“嘟”,每十二秒一次。三者交错,形成盘根错节,不断改变的复合节奏。只有不断行走,在空间中调整方位,才能与声波持续相遇。
很少有人知晓,山鹿是高原的邮差。我想写封信给你。在鹿角的复合节奏里,找到一根红色梁柱,用左手击打墙体,右手在柱子边缘直线处,记录间隔与声长,数着刻度寻声而动,直到写完这封信,投递给漫无边际的地下声场。明天你就能听到这封信。它挂在鹿角,掷地有声。
灰雁升空(037.5311 N, 112.3630 E)
我在这里学会飞行。这是天空之地,过渡之地,临界之地,灰雁升空之地。第二十五层,东山晴的最高点,也是整个区域的最高点。
我跟随传说的指引找到这里。我听村里的孩子讲,他们喜欢穿梭在空中过道,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个地方并没有想象中的难以寻找。挑一幢楼,选择一个楼层。从电梯间出来,同一层东侧和西侧的房间之间,有大约十米长的过道。前后没有遮蔽,裸露临空,气流通透,石板小桥一般,直直横跨。
径直上到最高处,坐在二十五层的过道。碧空青山下,东山晴第四期楼盘尚未完工,杏花岭其他社区建筑丛立,边缘模糊。地面楼群之上,有一座看不见的天空之城正在建设。远处吊塔隐匿云中,如同闪过的机械羽翼。有限的地面,无法呈现此刻尺度的巨大。我喜欢这里声音的广袤与虚无。声音被抹平了锋利凹凸,暂时剥夺了危险潜质。声响柔软,景象温和。如同远处滴下的墨滴,不疾不徐,层层推进,最终浅浅的晕染到耳畔。
是的,十米的过道看着有些狭窄。但这样的长度,已经足够一只大鸟舒展站立。鸟类驭气而行,不喜欢停滞稳固的气流。尤其是颈背修长,展翼宽大,飞行极快,几乎不受阻力影响的灰雁。它们终年都在寻找最佳的气流航道。东山晴的过道,早已成为鸟类繁忙的港口。清晨到黄昏,过道一层层往上,一直到最高处的二十五层,站满了等待起飞的灰雁。
第二十五层的灰雁,是高傲的雁群领航员。它们躬身引颈,细致远眺云层上空葱郁的声响。它们探明海洋的水流朝向,记住每一处暗礁和甬道,每一处鱼群和旋涡,每一处急弯与缓坡,每一处上升与跌落。这里是灰雁升空之地。我只是紧握栏杆,幻想一起飞行的人类。悄无声息的蹲在灰雁落脚处,趁着它们脚步摇曳的空隙,我用碳灰在过道的边缘,勾勒远方气象,想象旅程的颠簸与平滑,快速存档尚未发生的私人航行路线。
我开始想念我那位朋友。她总说自己害怕高处,害怕难以抑制纵身一跃的冲动。我想带她来这里。硕大沉默的灰雁会成为她的伙伴。灰雁升空,一手抓紧雁背,一手随风摆动。她的脸上没有恐惧,只看得到无尽飞行的沉迷。
2022.04.03
2021 “露台”项目 – 地方音景田野观察表

01)写下你此刻的名字 ,可以任意一个或多个
02)猜猜现在可能的时间,以你愿意的任何格式写下来
03)揣摩你所在位置的地理坐标,包括海拔高度
04)每隔一段时间保持沉默呼吸六十秒,什么都不做
05)感受并绘制此刻所在空间与身体之间的大致比例
06)不假思索写下来,与这个地方相关的多个场所名字
07)在空间内持续移动身体,同时画下来你的路线
08)凭直觉找几处让你舒适或不舒适的地方,站立或坐
09)触摸你遇到的植物,模拟其枝叶姿态,重新命名
10)记录你遇到的动物,模仿其运动形态,重新命名
11)抓一把土壤,感受湿度温度颜色味道,重新命名
12)随手捡一样物件,绘制形状记录材质,重新命名
13)连续抚摸离你最近的非生命体,描述你们的关系
14)快速记录此刻同步发生的多个事件,分别命名
15)感受并绘制现在你身边人群的数量、密度与关系
16)记录你此刻听到的或想到的故事,可以只言片语
17)用嗓音模拟周遭多种声音,画一画声波的样子
18)小声喊叫,对比测量周遭其他声音响度,记录差异
19)闭眼聆听周遭声响,记录你的情绪和皮肤反映
20)拍手,不限次数,绘制空间给你的回响以及影像
21)写下你感觉到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或多个神灵名字
22)虚构历史,回忆过去这里发生了什么,记录关键词
23)猜想并记录,这里一年四季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24)期待未来谁会来这里,就在此刻位置,给 TA 留言
25)环顾四周,口述此刻你身体内部空间的感受
26)把这个地方全部装进你的身体,绘制对应的位置
27)以你喜欢的方式,给这个地方命名,长短不限
28)不要停止,继续想象,给这个地方,再多几个名字
2022.04.03
2021 “露台”项目 – 想象的风景 I (念白文本)
想象的风景 I
从亭子的窗口跃出,以切片的方式,一次次瞭望。一个地方的土壤,砖石,草木,蟋蟀和鸟类,它们似乎都在某种运动态势中。旋转,发芽,生长,轰轰作响。戏台,寺庙,街巷,钟鼓楼阁。水井,耕田,宅院,崩塌抹去,宛若重生。
我们从土壤开始。转动身体,往下沉入。看得到听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全是土。这里的土,挖出来运走,又堆成土堆,摊开来夯实,又填平。黄土丘陵,每形成一英寸土壤,需要五百年的时间。湿润粘稠的土壤,每小时移动一根头发的宽度。土,是柔软宽厚的母体。村子的东南西北四个角,常年有土冒出来。有人收集这些土,放置在巨大的玻璃盒子。四个底座一百平方米的透明柱子,每个足足有五十米高。阳光穿过厚重的土壤,折射出上千面扇形的五色光。就在村子中央,涌出一座虚空中的白色佛塔。
再靠近一点。对面高楼地基的位置,藏着桥东后街27号院的五口窑洞。以前,人们住窑洞,冬暖夏凉,把家藏在土里。现在,我们手不沾土,凭空住在土之上。土壤因为真菌的帮助,转化为砖石。砖石垒叠咬合,顺着人的喜怒哀乐,长成建筑,切割了空间,形成脚下的村落。 我们呼吸,村落渐次摇摆,彼此紧密相连。
因此,搬到东山晴的老人,会随身在口袋里带一把土。胃口不好时,炒一把土吃。地下车库的东南角落里,还有人供奉土地爷。下雨时,小孩把土撒满空地,用雨水搅土成泥,以泥塑像。这个地方,土是人们的食物,人是土地的阴影。
土壤被规整,容易丢失记忆。脚下美术馆的土层深处,出土过“太原组”古植物化石。它们归属于早期中州华夏植物群。梭鳞木,斜方鳞木,卵脉羊齿,南票华夏木,长在逍遥期的地址时代。东山晴浅浅的土层下,用锄头就能找到燃烧的植物。村里老人习惯徒手挖煤,把煤放在院墙头,晒上一晒。有了煤,就能梦到已经消失的森林,火光和祖先。
你所看到的建筑的每一条直线,我们都用煤块,擦上了黑色的标记。在夜晚,灯光全息,高楼变成一块块边缘发光的巨大石头。每一条直线,都会折射远处东山的树影。新疆杨树、国槐、油松、侧柏,每一种植物,它们的影子都有不同的灰度。
但是你见不到杏花树。这里是杏花岭,却没有一颗杏花树。长江村的杏花,已经湮灭许久。这几年,每年都有人在屋顶补种杏花树。长长的根系,缠着人,穿过墙,直直下坠。傍晚时分,远远望去,花冠连成一片,以为天上红云飘落人间。那屋顶,也就成了戏台。
幸运的是,这个地方还能见到杂草。杂草与土壤结盟,与天空为友。杂草完全依赖鸟类,以及孩子散播种子。孩子们在每一幢高楼的天梯里追赶,顺手把种子从天空洒下。黄土铺满长江村,杂草在每一处边界疯长。它们长在土堆上,围墙边,电梯间,人群中。它们把缝隙填满,改变走道,影响心灵,指引水流。把眼睛贴近草叶,画出地下纵横河流水道,我们随时潜入月夜,泛舟远行。
有些草,能长一人高。每年九月,人们聚在一起割草,晒草,捆草。草堆积多了,依次摊开来,放置在美术馆通往住宅楼的长长通道,整个空间变得温和软糯。每天中午和黄昏,村民都会在这里乘凉和昏睡。剩下的草,到了冬天,人们会挑个日子,烧上一整天,烧给东山的神灵。漫天的草灰,安静了整个村庄。
有草的地方就有蟋蟀。长江村大概有一千只蟋蟀,蹲在幽暗的土壤深处,声波直达村庄边缘。它们吃草,也把草吐出来做肥料,供蘑菇生长,鸟群啄食。夯土造楼,并没有衰减它们的报时能力。这个地方早已没有了晨钟暮鼓。只有村里的蟋蟀,还能精准到每小时准点,保持集体片刻的静默,不分昼夜。就这样,蟋蟀掌控了村里人的身体节奏。清晨蚕食黄昏,在每一个静默时刻,人心此起彼伏。
有蟋蟀的地方就有鸟群。蟋蟀在深处。鸟群在高处。燕子衔草筑巢,燕子住在高高的神庙。神庙在村子的东边。因为缺少合适的木头,神庙里的雕像,改用彩色金属灌注,高低不一。孩子们争吵嬉闹,一次次从神像的肩部,顺着硕长衣袖滑到手掌。又从手掌上轻跳下来,摸一把香灰,再次爬到最高处,倾身俯瞰村庄。等到破晓时光,聚集的燕群咬着孩子的衣角,乘风鸣叫,依次滑过天空。
是的,孩子是村庄的信使。土壤,砖石,草木,蟋蟀和鸟类,才是这个地方隐藏的主人。此刻,站在封闭狭小的亭子里,借着从黑暗中偷来的几束幽光,我们可以在长江村的永恒时间里,一次次的张望,一次次的安静游荡。
2022.04.03
2015 “田野”项目 – 声响剧场演出台本
准备:每个手机都收都打开 荔枝FM,斗鱼,B站,映客,SAME
第一部分:进入房间 I am sitting in the Room (五到七分钟左右,反馈长音,诵读)
1. 目标:观念诗意。不同于原版本。直播意味着没有等待,只有直接的不断打断和重复。
2. 音源:一只手机收音,四只手机直播播放,形成循环。
3. 人声:现场诵读。
“我正坐在一个房间,和你现在所在的那个房间,不一样。我正在直播我说话的声音。我将在这个房间里,反复的聆听这次直播,直到房间的共振频率,不断自我加强,以致于我所说的,都被摧毁。也许节奏除外。你听到的,是经由我说话所激发的,房间自然共振频率。我并不把这个行为,当成是一个物理事实的展示,而更多是作为一种方法,用来消除我讲话里,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规则,不平整,或者错误。”
I am sitting in a room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are in now. I am recording the sound of my speaking voice and I am going to play it back into the room again and again until the resonant frequencies of the room reinforce themselves so that any semblance of my speech, with perhaps the exception of rhythm, is destroyed. What you will hear, then, are the natural resonant frequencies of the room articulated by speech. I regard this activity not so much as a demonstration of a physical fact, but more as a way to smooth out any irregularities my speech might have.
4. 行为: 坐着,缓慢。点开现场直播手机荔枝FM开始直播。打开四只手机收听直播页面(荔枝FM直播app搜索zafka进入直播收听页面)。朗读中文部分。每次一句。慢。自述的声音。等待声音自然消失。诵读英文原文。连贯读。不要着急。最后一句之后,中高频稍微持续一段时间。
第二部分:房间控制/呢喃情欲 (十分钟左右,房间规则诵读 & 观众ID诵读)
1. 目标:机械诗意 与 数字诗意。 私人情欲,与紧张代码诵读。从更冷静到紧张急速的诵读。呈现隐私与情欲背后的计算框架,代码决定。声音本身要形成一定的质地,以及演奏的变化起伏。
2. 音源: ASMR。斗鱼。 主播。映客。 游戏。斗鱼。
3. 人声:【代码诵读】直播页面背后的网页代码的诵读。去除意义。机械诵读。https://live.bilibili.com/697655?from=search&seid=10906530073945580992 B站复杂的投喂代。【ID诵读】 ASMR,以及主播页面上的观众ID诵读
4. 行为:站立,与设备交互,与观众交互。
A) 准备(2分钟):拉机械手臂,选择斗鱼,调音台加效果放大ASMR,效果器走reverb,调整到满意声音效果。同时右手边留一个手机打开映客,监视状态。B德叔无人声底噪专场;女生声音来一个。
B) 细流(2分半钟):张望,诵读半机械,界定房间。先用ASMR的声音铺底,每次诵读都读数字的代码行数。读房间控制。注意:声响颗粒程度,EQ调整,整体设定氛围。建立房间关键构成元素认知。房间,用户等。暂停键斗鱼ASMR保留app。
C) 独白/喊麦(1分半钟):激烈,诵读进入高频迅速,喊麦状态。读到弹幕例如容器循环渲染,切断所有ASMR,直接用映客主播声音独白,适当保留某些ASMR。聆听片刻然后切断,读相关打赏礼物的规则。循环进行。主播独白,可加入ASMR中的情欲人声(韩国爱心觉罗)。注意:独白和诵读之间,形成对话/喊麦,舞台前后台对比关系。建立初步控制关系。
D) 洪流 (2分钟) :穿越火线,主播房间,不停无规则切换MUTE按钮。增加声音效果。调节EQ,以及效果器控制各个preset按钮。声量增大。高密度冷静诵读监控屏蔽代码。呈现强烈的控制能力。注意:塑造空白声响,命令独白,以及嘈杂碎片。建立权利角斗关系。诵读冷酷。可使用第三轨话筒。
E) Drone(3分钟):reverb加最大+ 1sec+rev = 长音drone铺底,全部ASMR。外围站立诵读:桌子外围拉机械手臂。读房间号码,名字ID来到房间。诵读荒诞,激烈暧昧。补充诵读:欢迎每个人进入直播间。欢迎演出进入直播间,欢迎一切来到直播间。欢迎田野来到直播间。欢迎正常的,以及不正常的来到直播间。欢迎这即将死去的来到直播间。
第三部分:无之日常 (五分钟)
1. 目标:生存诗意。
2. 音源: 从人声到环境。身体:模仿动物叫(SAME) 啊啊啊啊啊啊啊 (SAME)。 情感:秘密树洞(或者日记本心情录音)选定段落(SAME)环境:声音博物馆 (或者耳朵去远行) (SAME)。
3. 人声:凯奇的沉默。关于无的演讲。第142页。到145页,以为未来是多么不确定。直觉的声响发声。
4. 行为:缓慢优雅安静的诵读。用三个手机,Same的app使用。 拉手机屏幕过来离自己非常近。把自己的头被屏幕包裹。就着声音的空隙,或者mute,或者偶尔效果器增加一点效果。一点reverb,1sec的delay。判断沉默的时间,内容的意义,现场混合各个轨道的出现。
第四部分:结尾部分 (4分33)
1. 目的:沉默诗意。
2. 音源:在一个全面被直播的语境下,沉默意味着什么。
3. 人声:一个沉默的主播。
4. 行为:各手机转到荔枝FM。手里拿着秒表,每过一段时间,就拉开机械手臂朝外一次。把四只手机的屏幕拉过去,直接对着观众。一起接受直播。把凳子搬过去,直接面对直播的手机站立。关闭调音台声音。
2022.04.03
2015 “田野”项目 – 作品设定笔记
“田之有野,音以为谋”。
一)目标:凝视的时间感 VS. 相遇的时间感
1. 一种在关系和运动中生成的时间感。在重返日常时间的意向与专注力,对世界的一种捡拾和补遗,在世界,社会和社群中流动的。
2. 行动的记录与超现实的演出如何并置,让超现实的象征场景成为串流中的节点,强调对政治的批判和对生命的考察,反抗系统与结构。作者如何意识到或者描绘出自身所在的生态关系,与观者共享时间上的无缝交换。内容本身是启动流通与联结的驱动力和向量。把行为的时刻放置在环境的日常,生成某种相遇式的时刻。尝试让自身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脱离特定的凝视而进入到历史的串流,以叙事的虚构,捕捉在串流中相遇的时刻。相遇的时间感,指向了某种联结与共享的生成,某种解放的时刻。
二)作品概念:机器聆听,无边田野 – 田@野 (SOUND BEAST / The Room)
1. 问题:在越来越个体化的高度风险社会里,游牧化的个体,如何安身立命?应该如何活?其中,媒介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人正借由媒介生产怎样的新观念和新行为,推动文化的演进? 随着包括公司和国家的组织支持的退化,因此借助媒介展开个体生存的能力要求更高了。不在把世界当成主体认知中的客体,也不再限制于集体认知所规训的世界规则。普世的价值,不是简单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同时也没有一个单一视野的世界。差异化的对世界的感知和体验的复杂构成,是常态。新的网络平台资本主义,是对传统组织形式的取代,提供新的社会规则,平台算法规则还在垄断中,在更可怕的监控中。更大的自由与更大的集权是硬币的两面。权力在更底层编码控制社会规则的生成方式。而大众比以往更加丧失参与和决定的能力。需要像一个数字动物一样活,高度网络化处理资讯以及身边环境,人和物。不断演化形变,即兴决策。或者干脆去掉所有的数字属性,重新回到最原初的生存技能塑造。因此,人应该成为无时无刻的创造动物,而不是整个现代社会所喂食的消费动物。创造动物,也就是巨型的吞吐之物。吞吐资讯,产生巨量的荒野遗迹。数字/数据废墟是新的文明开端。创造是习惯。而不是精英专属。这里的创造,意味着通过媒介开拓新的时间和空间,在时间和空间里,发生新的反应。不是精英式创造。
2. 主张:
A)成为一只荒野野兽,即兴的在所有的相遇里谋生。成为一只荒野野兽,通过生产,去创造现实。生产本身就是活着,存在。我们依靠生产,吞吐物,来标记节点。不是为了表达,而是存在,刺探,联结,反馈。这与动物在丛林的生存模式类似。持续的,大体量的创造。让媒介成为人本身。生活在数据里的人,成为可见的人。不在数据里的人,不可见之人。
B)声音媒介本身进入到日常生产工具。因为声音的生产,带来主体的塑造因为声音与权力的高度相关性,声音生产和传播的权利是被高度监控的。直到今天,跟视频媒介类似,声音媒介的民主化,也经历了从自我的表达,到内容的生产,再到社交关系的展开等众多维度。从文化的场景来看,声音进入私密性的日常生活领域,声音本身的公共性强制特征在弱化。直面当下全新声音环境,声音作为一种媒介的可能。
C) 重塑田野录音,聆听体验。机器聆听/数据聆听(田):无尽田野流,随机切换,超日常情境。关键问题是,规则是什么? – 混种身份/流动自我(野):流动表达,崩塌剧场,即兴主体。关键问题是,演出者的角色是什么,他和聆听以及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D)“寄声”有丰富的日常场景和个体叙事,对聆听和想象的清晰呈现,清晰的重构,日常生活的炼金术。创造的新体验,集中在高密度的语言和日常声场的激烈交互,相互聆听与对话,寄生缠绕。“声墟”是关于新声音文化场景下,主体塑造的呈现,仪式化过程,田野的游走,未被听到的个体。创造的新体验,集中在废墟般的网络声场世界,不同的个体欲望,主体的建构与崩塌。
3. 概念:
A)急剧变化的实时声场(田):机器聆听/数据聆听。如何切换和组织声音? 超日常情境的声场:无尽的田野,随机的切换。现场表演同时被直播。
B)主体身份的虚拟转换(野):混种身份/流动自我。如何形成主体与声音关系? 如何完成大数据量的吞吐,联结,塑造一个野兽现场的能力。 错误的机器主体:不要演。放弃主体。机器聆听,即为表演。表演如机器。 转变的聆听方式:聆听本身成为声场,聆听塑造主体。我听故我在。直播整个聆听。聆听之后的互动和应对变化,媒介作用的重新定义。
4. 原则:
A)重新定义田野:你所在的就是田野,田野不管你在不在。田野不需采集。不需要呈现。田野不是对象,不是素材。田野就是所有。四格为田。网络为田。野,田之所在。网络为田,野之所在。田野就是诗意。
B)重新定义聆听者:聆听者就是偷窥者。去主体的,流动的中介。机器和人,都是聆听者。主体的流动,人与机器的合一。聆听就是偷窥。
C)重新定义聆听:机器和人的交互,聆听的相互作用。基于生产的聆听。而不是消费的聆听。多线程聆听。跳跃聆听。混合聆听。反复聆听。在现场又不在现场的聆听。对人与机器混合体的聆听。机器和人的混合体。对数据的聆听。无主体的聆听,基于声响本体的聆听,而不是主体意识主宰的聆听。
D)重新定义表演:一切都是表演的,一切也都不是表演的。表演是瞬时的。人们在麦克风前的表演,是即兴的,随意的,流动的,随时消失的。在线不在线的表演。On &Off。表演是打开的。表演是去中心的。表演是不需要素材的。表演是设定相遇的时间。表演没有预演,表演是发生。
E)重新定义田野与表演:表演正在成为田野。田野正在成为表演。
F)重新定义人的介入方式:人不是表演的中心,人的作用,不是表演。人是表演中的一部分。
三)现场设置:机械人偶与无边界的田野
1. 黑幕剧场: 演出位置在场地中央。位置不在演出长桌。光源来自机械矩阵中的手机屏幕发亮。
2. 机械矩阵:1.5米左右高,五个手机依靠话筒支架构成的近圆形矩阵。矩阵不远处,有一只支架上的视频直播手机。手机背面有直播的二维码。手机的音频连线下垂,都联到矩阵中央的母体。矩阵中间,有一张高40厘米的小桌子。盘腿坐在矩阵中间。地面是打印的纸张,可以捡起来随时诵读。
3.人机母体:通过手机,连接进入调音台,调音台aux有硬件效果器,最后进入HEAT。有一只麦克风插在调音台上,声音可以被实时采样,实时重放和播放。播放来自手机的在线流媒体音源。同时现场人声。人体作为agent的发声。
4. 机械人偶:表演者佩戴耳麦。表演者脖子上挂着线材。线材一端直接落在调音台上。可触摸发声。全场站立。在最中间站立。游动。
四)音源构成
1. 在线音频: 模仿动物叫:SAME; 日常环境事件录音:SAME耳朵去远行 + 声音博物馆; ASMR:斗鱼,b站; 日记本心情录音:SAME秘密树洞; 啊啊啊啊啊啊啊:SAME;游戏虚拟世界声响:B站。王者荣耀。末日生存。我的世界。生化危机。
2. 音频处理:原声声音的EQ调节,以及效果器,多轨混音形成的soundscape为主;或者是对在线音频现场调变所形成的drone长音等
3. 现场人声:即兴的口语:以为梦,以为田野。环境的敲击:一切可敲击之物。田野。肢体的敲击:跺脚,拍掌。诵读的文本:事先撰写好的文本,现场的诵读。
五)表演原则
1. 即兴:强化实时直播特点。即兴的行动。自我与外界的反馈。链接,吞吐。声音的野兽如何生成。演出实时得到评论。评论成为演出。衍生的一切不重要的才是重要的。
2. 聆听:对0,1,0,1的数字解码的诵读;随机朗读所有的弹幕和评论文字。
3. 交互:站立游荡的机械人偶:无主体的主体。被线材拴在人机母体上。与环境的互动:敲击万物。与机械的互动:对铁杆以及屏幕的肢体接触。面对直播手机的对话,对屏幕的迷恋。迅速的触摸屏幕,转换多个声音来源,混乱的。机械人偶与声音母体之间的关系
2022.04.01
2015 “声墟”项目 – 声响剧场演出台本
包括了 “听,说,读,体,物,己” 六个部分。
【序】(T1采样。低音轰鸣。保持仪式。冷静,中速的读)
在声音的废墟里,消耗掉,复写的时间。在声音的废墟里,消耗掉,等长的时间。在声音的废墟里,消耗掉,消耗掉,消耗掉,这场演出。
———————————————————————–
【听】(T2采样。听见长音开始。关于自我聆听。注意跟随长音的节奏)
听。“误入。我这没什么可听的。你们听不听,与我无关。也许这才好呢。”你们是谁,谁是听众。到处都是麦克风,在公共和私人的边界里,在宇宙中心的黑暗里,我不再关心舞台。是谁在聆听,又与谁对话。而麦克风是随时闪光的镜子。任意的截取一个时间,随时的面对自己。发出点儿声音,我就存在。复制繁衍,释放舒展。在自我的摧毁和再生里,在自我的打开和收缩里,我就这样,度过时间。
(站起来)是啊,“这里,没什么好听的。”我只在乎生产。世界是我的回响,我是我自己最大的回响。身体的共鸣才是自我的舞台。哪里有什么听众。一段录音,只不过是一段蜕变的躯体。它无比真实,但又如何。所有的聆听都是即时的。声音的废墟里,我用录音佐证生命的丰盛,不断的把当下悬置起来。
(回到桌子)不不不,我应该说,录音,才是聆听,无关乎他人。在对自己的聆听里永生吧。至于聆听他人,那可是谦卑的劳作,不可及的恩德,沉重的罪与罚。我并非上帝,又如何能接纳整个世界呢?
你听,你听,你听。这场演出从一开始,你就在听,你们都在听。那又如何。“你们听不听,与我无关。”这里,没什么好听的。重要的,就是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是第30天。今天9月11号啦。今天是2014年11月25号。好像是时间到了。今天。现在是23点27分。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37分。一分钟怎么那么快呢,好赞呢。今天。2014年12月25日。你昨天晚上熬夜了,现在可能在睡觉吧。现在,是和他分开的第7个月。今天,是第333天。今天。现在是晚上的5点17分。这是我的第一个日记。我是否会坚持每天过来讲一段话。就是,看这个电台名就知道,果冻日常就是我的日常。给以后留一点纪念吧,也当做一个日记。我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录的。就是把每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都打算录下来,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当主播的梦想,但反正我是吧。Sorry我忘了,是什么。今天没有任何主题,也没有任何音乐,就这样晚安。现在是23点27分,我还活着,而且,并且活得很好。
———————————————————————–
【说】(T3采样,今天和日常的采样放完,结束在现在是23点接钟声敲响)
说。现在是21点05分,我也活着,并且活得很好。说。口述呼吸吐纳。沉溺在日常,我就是日常。来,说点什么,把该死的日常还给日常。来,说点什么。
“也许,诉说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而我的语气又容易使人昏昏欲睡。”。
“诉说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说。但我还是要说。说起来,要慢一些,能听到自己,看见自己。慢一点,感觉到自己。不是犹豫不决,而是无比的享受。长度,速度,重量。我们压低声量。怕惊了什么。说几句不重要,说什么不重要。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是口袋里晃晃荡荡无棱无角光光亮亮的石头。形状,质感,颜色,空间。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像一块温暖的水果糖融化在刺眼的阳光里。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就是水边奔向云间受了惊吓的雄性兔子。你刚抚摸到,他们就溶解。但我还是要说,说,说。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认识你的时候。边把她给的爱,当成一种习惯。”你说你不相信爱情。我不希望。曾经我们疯狂的追求爱情。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的无可奈何。可能刚开始太依赖他了。在一个难眠的午夜。在一次次的心动过后。现在一下子抽离你没有你的世界。爱情还剩下什么。是伤害,最大的伤害。我会苦恼。
【说】(T4缓慢爱情采样播放。在采样播放的同时,缓慢的说,迷离的样子)
说起来,再慢一些,听到自己,看见自己。再慢一点,感知到自己,享受自己。
———————————————————————–
【读】(接着T4。感觉到美好后进入)
读。选择一个文本。选择一个文本,开始读。诗歌,散文,小说,课文。(停歇,听)读,把自己扔出去,顺从一个文本,把自己展开,读在一个想象的呼吸里,另一个生命的节奏里。读,把自己扔出去,顺从一个文本,把自己展开,读在一个想象的呼吸里,另一个生命的节奏里。(停歇,听) 声音可以从容,在秩序里穿行。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物种。声音转换为记忆,而记忆转换为身体。重复再重复,生产带来改变。
没有月亮,面包甚至都不够,朋友更少, 如果你步入老年,先我而死,
只有一群痛苦的孩子。梓树和馨香。
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细雨中的日光,春天的冷,
破帽遮颜过闹市。秋天。
每当他看到,听到或感受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时,他就不由自主的感动,他就觉得非常的舒畅和亲切。
读。选择一个文本。A big mistake. 一个巨大的错误。I‘ll make a cake. 我要做块蛋糕。 I will make a cake for jack. 我要给杰克做块蛋糕。 I‘ll make a shake. 我要做杯奶昔。 I’ll make shake for jack. 我要给杰克做杯奶昔。I’ll make a cake and shake for jack. 我要给杰克做块蛋糕和一杯奶昔。 I I’ll take the cake and shake to jack. 我要把蛋糕和奶昔带给杰克。Opps.
———————————————————————–
【体】(T5采样播放。坐着评论,冷静)
体。(前面沉默聆听,冷静的尝试声音诗)如同呼吸新鲜的空气。失重,失序。打破,打破,打破。身体是座神庙,我是自己的祭司。扔掉语言。扔掉。扔不掉。扔掉。扔不掉。感觉到兴奋,也感觉牢笼。感觉到奔跑,也感觉到绳索。(啊啊啊啊啊啊)声音有多大的自由?你感觉到了吗?声音能有多大的自由?你感觉到了吗?换个方式探测世界,像一只蝙蝠,啊,啊,啊,啊,发出声呐,听到回响。不要停止,不要停止。沉默是死亡。声音是激进的生命。我就在这样在混乱和秩序里。不要停止,紧紧握住自己。不要停止。(站起来,英文叠唱部分,轻声跟读)
———————————————————————–
【物】(T6采样播放。聆听,开始触摸物件,敲击左面,抚摸麦克风,吹麦克风,嘴部发出咀嚼等细碎声音,边说边动作)
物。与万物对话。沉默,弃绝语言。抚摸,敲打。请求一扇门,让光照进来,把物件打开,打开,打开。咀嚼,吮吸。贴近,亲密。端详每一个物件,体味每一个动作。在你的耳朵四处,借由世间万物,治疗丢失的灵魂。这些细碎的,微茫的声响,这些细碎的,微茫的声响,这些细碎的,微茫的声响。
———————————————————————–
【己】(T7采样播放。站起来,站在另外的灯光下,跟随角色代入诵读) 己。Hey,大钧,Lopez,Paul,翁魏,施政,RMBit,史文华,徐程,长存,pink pilots。 你比你想象的伟大! 你是,WHO R U?
亲爱的一东,曾广。家毅。收购了吗?你受够了啊?你受够了吗?
你是谁,WHO ARE YOU。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伟大的声音艺术家。
深呼吸。慢慢的保持能力。确认一下。再次举手确认一下。你会感觉你的能量提升了一万倍以上。满心欢喜的接受。
像百万富翁,像千万富翁,像百亿富豪,像亿万富豪。
像百万富翁,像亿万富豪。像百万富翁,像亿万富豪。
【己】(继续站着。跟随读自尊宣言)
我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我。我的一切,都真真实实属于我。我拥有自己的一切。我的身体以及我的一切行动。我的头脑,以及我的一切观点和想法。我的眼睛,以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我的耳朵,以及他们所听到的一切。我所有的感觉,愤怒,喜悦,沮丧,友爱,失落,和,激动。我的嘴巴,以及由他说出的一字一句。或友善亲切,或粗鲁,无礼,或对,或错。我的声音,或粗旷,或轻柔。因为我拥有自己的全部,我和自己亲如手足。我学习跟自己相处,爱惜自己,善待,属于自己的一切,爱自己。
2022.04.01
2015 “声墟”项目 – 作品设定笔记以及田野工作分析
一)整体结构设定
1)作品核心原则:
• 设计一次完整的新的聆听体验。听觉的再造,与世界的再造,是同一的。重建生活的精神意识。整个展览是一个完整呈现。偏重学术化的。是对围绕声音自我建构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但整体呈现上,偏重剧场。拆解日常声音自我建构中的诸多元素,然后以展览的方式整体呈现。整体上把今天的声音自我,拆成不同部分/命题/问题,然后呈现为关于声音自我。
2)整体声场标准设定:
• 私密式的聆听经验:不是冰冷的,而是充满私人气息,情绪化
• 混合式的聆听经验:视觉,文本,声响,是多媒介的探索。
• 抽象式的聆听经验:不是对客观声响的呈现,而是解读和再造
• 间离式的聆听经验:不是对播放的简单聆听,而是适度制造距离,引发自我反思
3)素材使用原则:
• 人声本身比较容易混杂,不适合同时多轨。
• 尽量少的抽象声响;少的录音素材。少的写作诵读。
• 需要一些根据写作和分析之上的素材加工。除了一些,少做最原始的播放呈现。
4)叙事结构设计:
• 参照阿尔托《与上帝的审判决裂》,写作一个声音评论和虚拟叙事的《声墟》声响写作剧本,讨论声响自我与数字空间,分开数幕完成。
• 主要结构设计:完全按照声音写作和评论的结构来走,我自己的诵读成为关键声音,其他声音素材,成为与我相关的角色,与我互动和对话,以及声响设定。展览的空间,就是一个我缺席但是正在发生的演出。我的缺席,是通过声音的安排来完成的。空间即舞台,可以展示剧本本身,文字,符号等。正式的演出现场,是一个我出席并且扮演多重自我的演出。
5)呈现的核心想法:
• 【声音媒介与自我的关系正在重新定义】:人们正在不断尝试,以声音为媒,重新定义对话,聆听,不断重塑自我,凝视自我,疗愈自我,记录和表达自己,然后不断遗弃,转变和再造。“人们为何录音?如何录音?如何聆听?”
• 【碎片流动声音自我的建构有一系列的特点】:因为声音的大规模私人化记录,留存和传播,自我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碎片的,多样的。艺术家尤其关注,围绕日常物件,亲密关系,角色扮演,心情叙事,情绪游戏,语言练习等,人们正在如何录制,呈现,聆听和对话多样流动的声音自我。艺术家称这些声音自我为“唤醒者,麦骑士,涂鸦客,治疗师,洋语犯,口述癖”等。这些声音自我的塑造,又基于不同的技术介质,呈现出不同的仪式,符号,听觉特征,处理手法,语词结构以及文化含义。
• 【私人化的声音自我构成广阔的公共空间】:在这种大规模出现的声音自我中,私密性向我们敞开。我们正在改变日常声响景观和聆听的涵义,我们也正在改变自我塑造的可能性。
————————————————————————————————————————————————————————————————————————————————————————————————————————————————
二)田野录音素材基本类型分析
田野素材整理,所指向的声音自我塑造,可以大致分为六类,多个角色。
1.唤醒者:潜意识录音,自我励志,心理暗示等。关于金钱和权力。
2.涂鸦客:短小的情绪化录音,喊叫,表达,小疯癫,图文小游戏等。匿名/隐匿者。日常自我“ME”。面对麦克风,以语言和情绪,涂鸦的自我。日常的疯癫。失序,情绪,混乱。大量剪辑拼贴的片段比如笑声和关键词等;日常草根DJ,精神病系列,吐槽,喃喃自语的失控自我和语言结构等。
3.洋语犯:练习英文等外语的口语录音,课文朗诵等。关于文化的自卑,语词的符号选择,以及变异。
4.操控主/麦骑士:视频女主播,MMORPG类国战游戏的国战指挥。国王,女王。YY上的主播们,国战的指挥者,喊麦控场DJ。
5.治疗师:亲密关系的角色扮演,色气娇喘,日常物件声响录音,多来自二次元文化。ASMR和同人音声两个大类型。日常细碎声响,以及异性的呢喃,都带来听觉和身体的高潮。ASMR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中文译名“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是一个用于描述感知现象的新词,其特征是:对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或者感知上的刺激而使人在颅内、头皮、背部或身体其他范围内产生一种独特的、令人愉悦的刺激感。
6.口述癖:自己或者和朋友一起做的有关日常的叙事记录,心情记录,喃喃自语,匿名吐槽等。青少年私人小电台录音。
__________________
2022.03.13
2013 “寄生/声”项目 – 声音写作文本 (J-Fever小老虎)
Mar.06.2013 AM07:57 (女儿-家里-起床哭闹)
我醒过来,可不想把眼睛睁开。听那一个个词语,我试着在眼皮的黑屏上画画,画出萝卜,画出黄瓜,画出大葱,画出一双脚,那笔法如何,应该同女儿一样,公司开会用的小黑板上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东西,那些概念、数据、酷的,牛了逼了,烦死个人,复杂的,年轻的,貌似有趣的,一句诗罢了。“我不和你谈论人生,不和你谈论深奥玄妙的思潮,请离开书房,我带你去广袤的田野,去看看遍处的幼苗……”
我的老婆是个好女人,她的声音像磁带一样好听,此时两个孩子在听,我女儿,我。
去年的最后一天,做了个决定,我要夺回自己。做一个公司做了四年,衬衫穿起来越来越合适,我有了一个孩子。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件事,拥挤,拥挤,拥挤,拥挤,幸福感的拥挤,成就感的拥挤,我还是很瘦,对,没有脂肪堆积,甚至烫了头,鸟窝的下面是一棵树吗,树洞,松鼠,猫头鹰,我粗壮得可以容纳下一头熊的冬眠?
我的老婆拍了拍树干,决定把上午给我。这意味着,在之后的每个上午,我不属于工作,也不属于家庭,今日清晨的枕头上,一个纪录片导演诞生了。在女儿的哭声中,我是透明的。
Mar.06.2013 AM09:12 (吹风机/女儿/音乐-早上起床-家里)
用水把自己弄湿,用风把自己吹干,多么小清新的表达,配合着诺拉琼斯的慢板,所以我爱你,吹风机,因为你够粗野,你的呜咽声足够坚固和安全,没有了噪音,我的耳朵受不了,我的精神受不了,世界上只有吹风机,Candy受不了——她是公司里的一个女孩,善良,单纯,就是他妈的太小清新了,那种软绵绵的嗓音,甜甜地表达,我快拉肚子了。
让我死在叠音字里吧,有没有人考证过,为什么对孩子说话要用叠音字?我想采访一下保姆,请唱出:“小糕糕”,“小糕糕”,“小糕糕”,“小糕糕”,“小糕糕糕糕糕糕”,“小糕,糕,糕糕,糕糕糕,糕糕糕糕糕糕!”对,对!还有象声词,象声词!“嗵!”“嗵!”“一二三,嗵!”
我关上吹风机,褪去保护罩,望着镜子里一头蓬蓬乱发,香喷喷,拖鞋,幸福的表情,像个保姆,像一块Candy。
Mar.06.2013 PM05:15 (下午青公馆附近胡同)
脖子僵硬的直接反应,就是看天,四合院的当中,叫做天井,井底之蛙看天,房檐上的鸟看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推开门的意思,就是偷闲,闭上眼睛,一名侦探——我干过这勾当,当年在雍和宫,行走在胡同里,像个盲人,耳朵是镊子,捡起声音的毛发。慢悠悠的电锯电焊电钻打着麻将,这是胡同的悠闲,不是大厦工地的粗暴,不过大家胡牌都等着同一张“发”,发什么?发展呗。
该回家了,家里有人。
家里有人,该回家了。
Mar.07.2013 AM 06:20 (清晨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里)
清晨粘稠。从厕所到窗口。
一卷手纸刚好用完,我把纸筒罩在耳朵上,发现了远方驶过的火车。
行驶在粘稠的清晨,带头儿的孩子用弹弓紧紧拉扯车头,混小子们可以吸一口气,陆陆续续扒上去。
而列车长正在练声,音符在粘稠中散播为石子儿,跌落在枕木当中,铺了一路。
我低头看,小区里有人用树枝拨弄着纸堆,他在烧信?一溜烟,火灭了。他用树枝雕刻地面。那情景,让我想起公园里那些用大毛笔沾水,在水泥砖上写字的老人。好像从来都没注意过他们写的什么字,怎么就没注意过呢?
有人用火烧掉过去,有人用水留下讯息。
我想下楼去看看,如果拿树枝的人不介意,我想把手纸筒扔进他的火堆。
清晨粘稠,缓慢,不易燃。
Mar.07.2013 AM 010:12 (机场排队打车)
左手边10米,有四个人和我同一直线,两个人在谈论股票,一个女人拉着行李箱,打开了出租车的后备箱,扬长而去。
如一次橄榄球的完美进攻。
漂亮。
去年我学会了开车,之前我依靠老婆。从此有个数字纹在我身上,像被发配边疆,每星期总有一天禁止入内——这有个说法,叫限行。
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每个人都被严格编号,北京早已被拆除的城门再次雄立,对不起,今天编号3的人,不能进入2环。
招手,停车,开门,坐下,好运气,今天只等了30秒。
如果目的地也属于隐私,那么司机,这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为什么我这么轻易地就告诉了你?
Mar.07.2013 PM 04:28 (上海青公馆门内外)
这个世纪到来之前,我曾想拥有一间海边的屋子。不是为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吸引我的是:打开窗户,听见大海,关上窗户,听见自己。
后来我发现这件事随时随地,唾手可得。安定门内大街上,左边是外贸服装,右边是爆肚,我点了一根烟,走进公厕,马路上的人生海海,瞬时退了潮。而我几步一个转身,第二波声浪就顷刻沾湿鞋头,谁还需要马尔代夫呢?
由远及近的救护车声,打开了我的声音日记。女儿出生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走廊踱步,点根烟,打开窗,又关上。我渴望窗外的烟火世界缓解我的不安,又怕那份喧闹破坏这安宁等待,这焦虑像脆弱的婴儿,禁不住爱抚又离不开关注。不知多少个来回,窗户的开关,一声咳嗽传来——
蹲坑的人斜眼看我,这在公厕里走来走去的家伙,怕是打扰了人家排泄的清明。
不好意思。
Mar.8.2013 PM01:38 (上海青公馆客户workshop男士洗脸产品介绍)
文字杀死了语言的灵活。文案。案。除非把桌子用来敲,要不然跟耳朵有毛关系?
耳朵退位了。
说是退位,不如说是垂帘听政。年迈的君主耳聋眼花,逻辑也已离他而去,谏言的大臣,模糊了面目,消解了语言,抽离为一声声鸟叫,蝉鸣,顿挫抑扬的异族乐鸣——哪个声音好听,就准奏。
从美学角度而言,极迷人。
如果人民代表大会也是这么个审议,一口嘎嘣利落脆天津快板的提案在全国范围推行天津煎饼果子成为整齐划一营养早餐普度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膳食平衡,还犹豫什么啊,全票通过!
姑娘,在我这个只用10秒钟洗脸的粗糙“男生”耳朵里,你是一个声音事件。
或者说得不准确,但更好听一些(好听的话,往往不准确,准确的话,往往不好听),你是一次音乐会。
你也应该意识到了吧?那高跟鞋的慢步,是节拍器啊。
Mar.8.2013 PM07:51 (机场登机)
身份有声音吗?
有啊。
你的是?
噔!
他的呢?
噔!
那个穿褐色大衣的女人呢?
噔!
戴红帽子的那个?
噔!
抱孩子的那个农村老太太?
噔!
那对外国夫妇?
噔!噔!
哎?人家可是外国人啊,没什么不一样?
噔!噔!
我是个声音艺术家,公共空间的声响多么乏味和单调,而且粗暴!为什么每个人不能拥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辨识声响?哪怕是不同的音符?还可以定制,我的是鸟叫,你的是汽车喇叭,他的是鼓掌,有一天你在机场听到过去恋人的身份辨识声音,回头望,慢镜头,这甚至可以改写偶像剧的剧本!我要倡议,我要行动,我要制造不同!
干嘛呢,快点!你该登机了。
噔!
Mar.8.2013 PM10:07 (机舱内等待起飞)
挣扎开始了。
低语交谈步兵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手机口哨罗宾汉,金属扣安全带摩擦剑客,在发动机和轮胎营造的巨大轰鸣围场中,一次一次刺穿着绵续的悦耳流俗放松小调。
这种斗争是无意义的,几分钟后,一切都被抹除,只剩下引擎的冲刺,划开空气的爆破声,宏大永远意味着淹没。
不过还好,起飞状态只是那么一会儿,就像升国旗,只是一首歌的功夫。
全体肃静,有多无聊。
Mar.09.2013 AM10:28 (打电话劝解关系)
当你用言语,试图解决远方的摩擦
更多的摩擦,却发生在此刻的脚下
Mar.09.2013 AM10:30 (一秒钟截取的电平声)
马季有个群口相声作品,叫《五官争功》,讲的是五官打架,争谁最重要。在修辞方法泛滥的语言艺术中,都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词语的皮肤,包袱,都是X光眼,直接看到包的是什么,包袱本身呢?
眼睛和耳朵,谁重要?
我们生活在,由眼睛主导的世界——这个结论可以用一座图书馆来论述,但就在上一秒中,我启动录音装置旋即关闭,意外发现了眼睛比耳朵厉害的关键奥秘。
在乔布斯将用户体验这个词安装在这个时代之后,用机械标准衡量肉身,眼睛天然具有一项简单至极的功能,而耳朵没有,那就是“开,关”。
凭此功能,眼睛占领了时间。
“一眨眼的功夫”
“眼睛一睁一闭,一天过去了”
……
沉默也不是开关。
我只好用手里的录音装置,“眨”了一下耳朵
Mar.09.2013 PM04:10 (家里室内规律电器噪音)
密室里,灯光昏暗,几人,出汗。
迷宫一。
“对空气的鞭打和牵动之精准,绝不是人力可能达到的,”巴赫说,“我发现了其中的节奏规律,这规律太过精准,我在钢琴上也许可以完成,但……”
大侦探已经沉默了一个上午。“我同意,尽管夹杂着两声老妇人的闲谈——”
“——但._他_们_不…属于_同__一个_____维度。”霍金的电脑显示如上信息。
“这种程度,我们小学有一半的人可以达标,保持匀速跳绳没有问题。”花园村第一实验小学体育老师丁大力表情严肃。
Aphex Twinz露出标志的超自然坏笑,他终于可以不用凭借PS技术,而用人脸做到了,为此他去了趟韩国。“丁,my bro~请你丫的让学生用乒乓球模仿一下我的IDM作品吧!”
“你去找校长吧,只要符合素质教育,可以先从Drum’n bass开始。”
Mar.09.2013 PM04:50 (剥瓜子等电梯)
视觉的世界快被穷尽了,3D是多么愚蠢的小丑的把戏,方向反了。
不要太多,少一点。给我留一半,好不好,你把该干的都干了,我坐在那里2个小时,干吗呢?
未来的影院属于耳朵。保守一点,很快会出现,只属于耳朵的影院。
第一次听这段录音,你是什么感觉?当时我身处这段声音之中,寒毛惊悚。
等等,我突然记忆模糊……
“我是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空旷,阵风——我折断了什么?还是剥开了什么?我在嚼碎什么——巧克力?薯片?膨化食品?瓜子?不,有个男人,我不是一个人,对!他在用脚踩,碾磨,揉碎,他在踩玻璃!他控制地很好,一下一下的,我感到不安,他知道怎么折磨我,因为,因为……那是我的眼镜!他在踩我的眼镜!我为什么不动呢?我被绑住了……不,不,别走,你到底是谁……”
属于眼睛的电影还会存在,但电影工业的流程会彻底改变。由声音师和配乐师主导和先行,编剧在黑暗中反复地聆听这2个小时的声响,终于拿起了笔……
Mar.10.2013 PM07:37 (女儿玩儿瓶子)
一秒钟前,客厅饭毕,谈心的谈心,说笑的说笑,瓜子、花生、电视,电脑,收拾着碗筷,这时只见地上滚过来一个瓶子,又爬出来一位姑娘,年方一二, 半低头,把瓶子滚了起来,几声, 煞是奇怪:只是一个瓶子,到她手里,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以的。又将瓶子拿起来使劲敲了几下,方抬起头来,向四处一看。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比皇帝出巡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当今世界,之于我,最伟大的打击艺术家,my daughter。
Mar.10.2013 PM10:10 (看演出台上台下)
今宵十点十,我身处俗世。感三界奇鸣,踱三生大道。笛径,曲折,和寡,盘山;雷池,滚滚,哀鸣,入地;酒场,喧嚣,窃窃,大隐。吾从何来,欲往何处?栖身于音丛,回旋于断续,辗转腾挪,好生跌宕!
跌宕!跌宕!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跌宕!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跌宕!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跌宕!
come on!跌宕!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跌宕!跌宕!跌宕!跌宕!跌宕!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跌宕!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跌宕!跌宕!come on!跌宕!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跌宕!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跌宕!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跌宕!
跌宕! come on!跌宕!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跌宕!跌宕!跌宕!
come on!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跌宕! come on!come on!
come on! 跌宕!跌宕!跌宕!跌宕!
Mar.10.2013 PM11:26 (演出录音)
宏大如何成为宏大?
此时一座宫殿正在建起来,所有人的耳朵成为地基。
宏大变成洪流,崩塌倾泻为单调。
险些被淹没之际,周遭几句低声闲谈,如抛来的绳索,拽我上来。
宏大是种霸权吗?
没了杂音,再丰富的编排亦是一律。我习惯了游击战,打洞地鼠,松动地基。
宏大带得走吗?
入睡前,我反复观看这张宫殿的照片。将音量调得最大,仍能达到慑人的效果。神像望着我。
Mar.11.2013.PM 07:08 (客厅厨房电视看孩子)
女儿望着电视的方向,那里开了一个洞。
邪风呜咽,魑魅魍魉。那声音不属于妈妈,也不属于阿姨,不属于锅铲,不属于小皮球和拖鞋。我心里着急,怕那里面危险,一闭眼,替女儿先进去了。当头撞上沙魔女,她和我一样犹豫。
“有异心的人,还是早点铲除的好。”
家里开了好几个洞,我焦虑得很。电脑、电视、收音机、电话里的声音,和我手里的杯子,打开的窗户,不在同一维度。复制、虚拟、传播,走廊过多,真实藏在哪个房间?
当我正在这繁复的音源迷宫中迷失,女儿却貌似没有我这么迷惑。她盯着那个洞,没一会儿,就将目光转向了厨房。那是比声音更具吸引力的食物的香味,她跌跌撞撞地向那源头走去。
Mar.11.2013.PM 07:51 (家里极安静开灯)
宝贝
白噪音,这最温柔的安眠曲
可否忽略,蹑手蹑脚的父亲,关灯
那清脆的开关声
有没有打碎你梦中的蛋壳?
Mar.11.2013.PM 07:57 (鼠标点击键盘)
这种圆形手斧非常适合刨光,和一般斧子不同,我用它侧着削,时而发出锯子的动静,有时又像砂纸。一艘小船的外侧,需要持续工作半个月左右,这只是刨光。
凿子我用得很轻,在船底丈量一下,“哒哒哒”一敲,刻些小孔做记号,因为船底板用的都是有树节的料,我要在树节周围插上些细小的竹条,竹条会把树节的缝隙填满,防止渗水,也可以把竹条削得很细,直接钉进去——我给你钉一根啊~“滴滴滴答答,哒哒,滴滴~”
鼠标和键盘造不出一艘真的小木船,但可以造出一次造船的过程。
Mar.11.2013.PM 08:33 (电水壶烧水)
“Empty your mind,be formless,shapeless,like water; and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it becomes the cup; you put water in a bottle,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water in teapot,it becomes the teapot.Water can flow or can crash.Be water,my friend.”——Bruce Lee
你把握了水的态,却没有诉出水的音。
听那走向尖锐之尖锐的怒吼,可远远胜过你那标志性的怪叫啊——关键在那一收,由狂沸转空寂,大开大合,收放自在。
Mar.12.2013 PM08:05 (家里新闻联播厨房收拾)
让声响具有政治性,最显性的方法就是新闻里的政治宣传,而那些隐形的呢?我在“听不见的城市”里曾探讨有关“声响的政治学聆听”,探讨城市中喧嚣和死寂背后的深层原因,关乎规划,关乎资本,关乎人的生存。而荒谬的是,新闻里单调的播报,已经模糊了词语的表意功能,变得语焉不详,正如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个体,对于政治的参与无力。此刻最真实的,倒是妻子给女儿洗澡的水声,相比电视里虚弱的掌声,更能触摸到生活的真相。北京现在有多少栋楼、多少扇窗户,正亮着微弱的灯光,漫不经心地笼罩着新闻播报,正被煮水、做饭、剪指甲、嬉闹、擦地板、亲吻的杂音突围,更多的时候,他们相安无事,毫无关联,这生态充满生机,却也令人沮丧。
Mar.12.2013 PM11:55 (午夜安静钟表声)
深夜上山,五官放大。只有手表的声音规律依旧,提醒我还拥有一点人类文明的理性可依靠。神秘的蜜,就是对密不透风的静谧的撕裂,那不安的鸣,莫名其妙,蜿蜒如山道。
冒险,就是毫无准备投入未知的危险,失灵的经验,就是想解开的安全带。我像个真正的盲人,不想习惯黑暗,只能闭上眼睛,连一点轮廓都不去把握。无所依凭,细微才逐渐肆无忌惮,变奏,变形,变异,膨胀,夸张,直到心被揪紧。
Mar.13.2013 AM10:52 (胡同聊天磨菜刀)
上午的胡同,依旧蜿蜒,杂乱,声响却相对清晰。相比马路的噪杂交响,胡同声场更像民乐对话,此起彼伏,错落有致。金属片互相撞击,心照不宣的原始广告,帮您打磨菜刀和剪子,让它们保持锋利,维护日常生活的饭菜品质,捍卫平淡如水的秩序,别出乱子。而吆喝声从何时已经消失?作为一名北京的移民,对那“磨剪子嘞~呛菜刀~”的叫卖倒也不太陌生,可下一代北京原住民,或将永久失去这种声响和记忆。磨刀人渐远,新的声音上台,早上见面,聊几句家常。随着拆迁,老邻居消失在高楼,对门之间只剩楼道的空旷混响。以往这种对话,往往伴随蝉鸣,自行车声,节奏不定,但亲切,舒服,太平,有粘性。汽车的警报装置和倒车提醒,自然地介入了谈话,成为可以忽视其刺耳的伴奏,这近些年迁至于此的工业移民,面目模糊地融入了平房之间的狭窄小径。
清晨的三重奏,潜伏着时光的流变和城市的异化,如同层迭推进的浪潮,一波送走一波,愈加嘈杂,却注定干燥。
Mar.13.2013 PM09:39 (家里嗑瓜子)
坐在电脑前,我用牙齿嗑开坚果,据说多食坚果可以明目,但眼睛再好使,也看不到声音的色彩吧。声音有情感吗?我不只是指乐音,它们已经被大众审美和调性法则所固定。比如,一本书掉在地上的声音,是喜悦还是悲伤?是积极还是消沉?一本字典落下和一本小说的下落,有什么色彩分别?
此时我正在房间里嗑着坚果,声音清脆,易碎,在空旷的混响之内。以往这种脆响,通常伴随着电视、闲谈、茶杯的碰撞和打火机的摩擦,而现在是它的独奏时间,只有偶然的一声干咳陪伴。仔细听来,每一个坚果的破碎都不相同,房间成为山谷,从未发现这悠闲的零食之音,会如此孤独和伤感。从这个时刻开始,它不再是热闹中的点缀,而是思索之痛的绝妙象征。
Mar.14.2013 AM08:09 (家里孩子海马玩具音乐)
用什么方式,叫醒一个小女孩?
我按下开关,女儿的屋子便里洋溢着MIDI音乐的简单,模拟的水声和气泡声,仿佛暗示着,她将要从梦境的潜意识中缓缓上浮,果然,她打了个哈欠。短暂停顿之后,一首新的乐曲响起,节奏略微变快,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这款闹钟,是婴幼儿产品专柜的推荐产品,千篇一律,令人无可拒绝。在柔和的经典乐曲中醒来,总比在汽车喇叭中醒来好,毕竟,我没有一座森林可以围绕她。
女儿睡眼惺忪,已经到了第三首曲子,还没有要起床的意思。在她今后的无数个清晨,会是什么声音伴她醒来?繁重的学业,匆忙的生活,柔和的乐曲恐怕无力,还是单调的高频响铃,才能令人生厌地把人从温柔乡拽回来。很少有人对梦中的声音有记忆,甚至有人猜测梦境是个无声世界。不得而知,我只希望女儿能多睡一会,我也能栖身在这貌似温柔的MIDI音色中,让耳朵重回襁褓。
Mar.14.2013 PM04:00 (地铁)
为了避开高峰,我早出来一会,溜达到北新桥上了地铁。有句惯用的俗话,常用来形容公共交通工具的拥挤,叫“挤得跟煮饺子似的”。现在下午四点,地铁大锅里的饺子不多,水的沸腾声倒听得格外清楚。车行,开始加速,速度的摩擦产生的呜咽,到达极点时放声大哭,随即渐弱。乘客零星的闲谈挣扎了出来,好像是对痛哭的列车的一种安慰。
这种地下的移动方式缺少真实感,除了个别站点人流的疏密,听起来没有太大区别,只有站名的播报证明了位置和位移,但如果不回到地面,便无从确认。经过十多次沸腾和痛哭,我有些爱上了这感觉。
Mar.14.2013 PM04:47 (办公室休息放音乐聊天)
办公室可以放音乐,谁想放就放,这是除了家庭以外,我唯一可以介入的公共空间的声场。每当听到Hiphop音乐,我就想起小老虎,尤其是现在,我多想他能在这里,不是让他演出,是让他看演出。两个女MC的说唱,游离在律动的节奏内外,有广式断句,北京脏话,模糊不清的家乡口音,口沫横飞的描眉画眼,真正的街头叙事,虚虚实实,两人的嗓音泄露性格迥异,却配合紧密,话锋密集,好似经过排练。
在这胡同小屋,声音是棵树,它的庞大和荫蔽,容纳所有肆意的共谋。DJ不厚道,说停就停,一棵大树如同遮阳伞般被折叠撤走,留下光溜溜的姑娘在众目之下,闭上了嘴巴……
Mar.15.2013 PM08:16 (派对嘈杂生日抽奖)
上接:人声鼎沸,沸沸扬扬,洋洋洒洒,洒洒万言,言来语去
下续:茫茫人海,海沸波翻,翻来覆去,去去就来,来来往往
横批:谁是三月十五生的呀?
Mar.15.2013 PM09:41 (出租车听篮球相声)
声音的旅行不可预期,谁能料到我打开车门,直接进了五棵松篮球馆,用不到一秒的时间,就坐在电视前,看一场惺惺作态的相声表演。当然,这是声音的旅行,实际上,我和司机坐在相对隔音的车厢里,行驶的动态模糊,收音机填补着我们之间无声的尴尬,而那瞬间移动,也仅仅因为司机女士精神紧张,轻旋按钮。她专注地看着前方的夜路,我疲惫而茫然地闭上眼睛,这些表演是不成立的,如同坐在剧院最后一排的观众,他们捕捉不到舞台上的面容和细微的动态,很多时候,只有声音是成立的事件。此时此刻,我和司机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朦胧的位移,和真切的电波。
Mar.16.2013 PM07:33 (看话剧开场)
他们用脚摩擦木地板,打着打火机,走来走去,渴望着,也让观众充满期待。我身处剧场,在第一声台词被说出来之前,当观众的笑声出现之前,戏剧性,还没露出声音的狐狸尾巴——这是个自负又自卑的判断,自卑在于,我无法确凿地分辨日常声音的做作与否。
台词为什么可以要让人听清?这是演员的基本功,也是剧本传达信息的需求,哪怕说得再轻,也要保证清晰,临终的遗言,耳边的悄悄话,如果需要让观众听见,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依然可以得悉这种超现实的秘密。
这是条狐狸尾巴。如果没了这条尾巴,人们游览动物园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Mar.16.2013 PM08:24 (话剧口风琴)
一声恰到好处的咳嗽,就在我的耳边盛开,咳得如此精确,押着台词的节奏,成了提醒,成了one two three go~~~~~~~~史上最短的定场诗,绝佳的短传助攻!在幽怨的口风琴和幽怨的女主妇之间,他是场下的阳刚冲剂,缺席的无奈把戏,冥冥中的互动喝彩,让我拥抱你,咳嗽!凭此一声,便给了我走进剧场,而不是电影院的全部理由!因为你的痰里,包含着最迷人的,只属于现场的,意外。
Mar.16.2013 PM08:44 (话剧唱歌)
女人唱了起来,和声有两个含义,相遇,和同行。女人声音坚决地说,不扑过来,谁知道会是什么?灯光熄灭,余音绕梁,黑暗中的换场,粗暴而突然,有墙被推倒的声音,听起来命运扑了过来,听起来就像女人被男人扑倒,粗暴而突然,观众开始骚动,情节还未展开,这些动静,已经传递了不安。
Mar.17.2013.AM10:31 (家里看新闻哄孩子)
耳筋急转弯一道。请听题!
……
好,请问,以下哪种是真实情况:
A 我是一名记者,正坐在人民大会堂,听新闻发言人的开场白,等待着采访。奇妙的是,这一届政府更有人情味,发言人的妻子也来到了现场,就坐在他的身后,哄着他们刚刚六个月大的女儿。这一切都提醒着我,眼前的这个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有家庭,有温情,而不只是一个喇叭。
B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Mar.17.2013.PM11:18 (家里深夜杂声持续)
晚上11点18分,这是唯一确定的事
我撕开了什么
我扔掉了什么
我在等待
我不再等待
没有什么可等待的
有风
那呼啸一直在
不是呼啸,是呼吸
不是呼吸,呼吸是可以听见的
我在呼吸,我是变化的
我在走路
并不是
我只是在摩擦地面
我没有任何对自我的描述
情绪的
内心的
不,我在描述
我没有描述声音本身
我打了火
我打了两下
三下
有一下很轻
很容易躲藏
女人的喘息
很容易躲藏
时间流,最后的排在最前
最后就是结束
通常是咔嚓一声
就真的没了
时间流,声音流
并非这么稀疏
我尽力了
我能留下的
就是这些了
捡起来也拼不上
在时间流上
那些波形
就像是这片空白上的污迹
就是这么一列
污迹
Mar.18.2013.AM10:15 (儿童医院小丑叔叔)
站在幼儿园的门口,我目睹一起强制外交。两个大人在攀谈孩子的去向,带着烟味;孩子们在咿咦呀呀,透着奔跑——“过来!”我看其中一个孩子被挥挥手召唤到了边境,心里紧张了起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如何交流?烟味的询问发生了两次,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孩子生涩而畏惧地开了口,“草莓幼儿园”,像背诵英语单词,一个字母字母地蹦出来,在爸爸和叔叔之间,孩子终于举起这不可逃避的回答的白棋,被披着温和语气的强势问话所占领。还有地方可逃?咿咦呀呀的国度里热闹不减,他眷恋地望着那里,却只能无奈地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渐行渐远。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开始重新审视我的外交政策。
Mar.18.2013.PM08:00 (嗑瓜子哄孩子)
傍晚的客厅,我嗑着瓜子,咔嚓咔嚓,像在打卡,打卡就是上班的凭证,瓜子是我在这个家的证明。绝大部分时间,女儿属于她的妈妈,女儿属于保姆,保姆发了言,陈述的尿布,是尽了职责的辩护。我在哪呢,我在瓜子声中存在,这不是靠边站的无所事事,你可以理解为爱的旁观,尽管我一言未发,尽管我远远,尽管我幽幽,但我在,我打了卡,不用跺脚或咳嗽,或是蹲过去,咿咦呀呀,在瓜子声中,我不尴尬,我嗑故我在。
Mar.18.2013.PM08:24 (孩子玩儿ipad乐器)
符合规则的,叫演奏,生出来的,叫“音乐”,不符合规则的,叫乱弹,生出来的,叫“乐音”。我女儿的小手落在ipad的屏幕上,这模拟的古老音色透着不伦不类,但根正苗红。音乐和乐音,一个先天,一个后天,后天的家伙有血统,抄起菜刀猛剁钢琴键,发出来的,也是乐音,因为有钢琴在。抄起脑门,迎向菜刀,却有可能剁出音乐。我也不会弹啊,为什么一定怀疑我女儿是肇事者呢,还是血缘关系漏了陷,孩子他妈那一声关切的“啊”,暴露了陪伴,有陪伴,必有主犯。
Mar.19.2013.AM09:18 (隔壁小学操场出操)
家周围有个小学,每天都能路过,偶尔把耳朵放风筝,飘到操场上方。中国的体育老师,每天都能享受里芬斯塔尔纪录片中的纳粹盛景,方阵,指挥,统一的步伐,动作和口号,幼小的孩子,单纯的服从,聆听自己粗糙的嗓音通过扩音装置,铺满整片操场,溢出校园,流到周围的民宅和马路。相比那些台下只有三五名观众的实验音乐探索者,体育老师可说是成功的人声噪音表演艺术家,观众的规模和互动性之可观,如同“一二一、立定!”的口号般不可置疑。那声音如此具有魔力,同化,追踪,烙在记忆深处,为四肢编程。我终于渐行渐远,远离了体育老师的频率发射范围。最可怕的科幻电影,就是疯狂的体育老师改造了扩音装置,幅员辽阔尽在掌握,我拧开汽车的收音机,“一二一”就从里边喷了出来……
Mar.19.2013.AM10:46 (老外同事讨论宠物)
离午饭还有1个小时,我饿了。公司的外国同事正在讲述,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充当听众。屋子方方正正,缺少一个灶台,食材都齐全,可以开烹。说话的这位,中音,咬字清楚,节奏舒服,像牛排或鱼,可做主料,本就新鲜,不用太多调味。于是我只笑了一声,拐了三次,手腕轻抖酱油瓶,最后一甩完成勾汁儿~女孩的嗯嗯两声,两片姜,另一男听众呢喃一句,葱花若干。这种菜相对好做。如果主菜不够诱人,不够硬,就得交相辉映,相互搭配。
并不复杂,日子久了都是厨师。但胃口要好,一天三个会议加五次闲谈,肠胃有点受不了。
Mar.20.2013.PM12:21 (胡同院子下雨)
城市里能听到的自然声不多,中国人讲风水,风和水,这里还是有的。通常情况下,风是管弦乐,水是打击乐。风雨交加,是难得的音乐会,不下雨的时候,偶遇这种没有拧紧的水龙头,我也很珍惜。水滴落铝盆,胡同节水措施,开场的小军鼓——行进的正步。旁落在待清洗的陶瓷碗碟中,丝毫没有油腻之感,化做可以捞起来的轻灵——点缀着散步。妙哉,偶尔经过的自行车轮,穿梭而非压过,一两句叫嚷是过门。声音的旁听者,我,把住了脉,决定大胆一试,介入这交响。随着水龙头被拧开,高潮突兀到来,水落在不同介质的分别变得模糊,乐音交叠,劲往一处。路人见我洗手,谁识这位指挥?
Mar.20.2013.PM06:49 (开车回家听音乐唱歌)
回家的路上,我通常不会跟出租车司机交流,车厢气氛冷不冷淡,我不在意,碰上喜欢攀谈的司机,有时觉得是种侵犯。放音乐的司机这位是一个,跟着吹口哨和哼唱的倒不多见,这是首没听过的歌,他的口哨有点走调,气息不稳,哼唱时嗓子撕扯,倒是唱准了一点。准不准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下意识地开始用规范来判断他呢?什么是规范?难道这首我刚刚第一次听到的歌,就可以成为我用来衡量司机歌唱水平的尺子?这个问题不解决,KTV的存在意义就不得而知,而歌唱的意义也值得怀疑。司机,请你再走调一点,再漫不经心一些,其实你唱得好多了,洗尽铅华的布鲁斯大师,脱了取悦的外衣,露出干瘪的脆骨,吹什么口哨,你是在吸我偏见的骨髓。我的耳朵靠得住吗,你的音响靠得住吗,也许窗外的鸣笛也不真实,前边本没有人,你鸣了笛,我就觉得拥挤。没有准不准的问题,你就是作者和问题本身,而我对你们都不重要,就像音响里的人忘情地吼,你头也不回地哼,此刻你们皆忘我。
Mar.21.2013.AM10:16 (家里洗完澡拍身)
北京冷得突然的卫生间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些老年的迹象。拍拍胳膊,和腿,和肚子,摩挲,涂抹,这些油让我发热,暖和,润滑,不干燥,我变得需要保护,我需要变得保护自己。我想起小区里那些拍击自己身体的老人,他们整齐划一,笃信着咒语:“超长能量,就在身旁,思维集中,全身通畅……”每拍一下,都像中了一颗流弹,机关枪吐着火舌,我的身体是辆观光三轮车,您瞅准了,前边就是百花深处,气功老人张安定,在非洲的碎拍中找到了真正的安宁。一直以来,削尖的只有耳朵,麻木的却是整个躯体。那些关节,女人已很少抚摸,和平的年代,没有拳脚相加。屋内料峭的春寒,把我安排在民乐团的左后侧,叮叮咚咚,耳朵选择性失聪,对不起各位,我迷上了听自己。
Mar.21.2013.PM08:57 (打嗝电热水壶沸腾)
一个饱嗝甩在墙上,再把一声咳嗽挂上去。游击队,放了两枪而已,连天气预报都算不上。暴风雨来得突然,熔岩暗涌大地震颤,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当头一棒。拖鞋分明蠕动在温馨的居所,是谁施展魔法,刹那开展了远古的洪荒?我,就是答案,你们,要继续不安。高频开始出现,愈加尖锐,低频层峦叠嶂,险象环生。沸腾吧!沸腾了,就踏实了,熟悉了,就不可怕,随着咔嚓一声,电热壶里沸腾的开水营造的世界末日已被辟谣,我这位声音的魔法师也成了黔之驴,在老虎面前不再面目可怖。
Mar.22.2013.PM12:07 (胡同观光车队和其他声音)
我路过七荤八素,众声喧哗,我站在世俗里。这不是胡同,也不是大街,是生活。中国没有好的小说,因为生活中少了世俗。精英排斥世俗,以超脱为志,屈原投了江,陶渊明进了山,知识分子蜷缩在咖啡馆里,偶尔挺身卷入民运的波涛,那是大声势,不是真嘈杂,嘈杂才是生机,给点小费才是对我们服务最大的满意。当尖锐锐的砂轮打磨声险些刺破耳膜的那一刻,我悟了,什么先锋自由爵士的即兴,无非也是照葫芦画瓢,这复杂而精细的总谱,我不正站在其中吗?
Mar.22.2013.PM05:38 (老外谈青年文化科技)
下班前最后的workshop,一位操着英国口音的女士给几位中国男女陈述关于日本青少年文化的生态,真正的英特耐神牛。陈述中透出犹豫,直到被一个纠正打断了口误,不安的节奏舒活了筋骨,有了些感情。我走神了几次,因为屋里某个角落正流窜着微弱的电子信号,滴,滴答滴,滴滴。在伦敦直飞东京的客机,空中小姐递给我一杯白水,告诉我现在飞机正飞过中国大陆,我忽视了她甜美微笑的红唇白牙,用多年的刑侦感知,地毯式搜索着定时炸弹的方位。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
Mar.23.2013.PM07:07 (连客谈社会化协作)
隐身时间。沉默是隐身的一半,如果没有我面前这位,略带台湾口音,发音清晰,慢条斯理,逻辑清晰的speaker——一前边那些定语都可以略去,关键是keep speaking,他在说,我的沉默才有意义,隐形才可达成。这是有益的,他在明处,所以充满了破绽。社会化写作?分明是一个人的演说。你也说了,嘴唇上下一碰,肯定不太分明,所以我没法领会部落里的概念,那是需要我拿着火把,或者用尖棒猛捣地面,和赤身裸体的兄弟姐妹共舞,才能心领神会的意境。你太文明了,不自信,没有温度,无法说服。他的声音空荡荡在房间里,像一只挥起来的手,有人跟着举了起来,成为了调查结果,却不是野火。
Mar.23.2013.PM10:55 (放水洗脸)
人鱼传说(上)
打开水龙头,放水,捧一把,把脸放进去。像游泳前把脚伸进池子里,试试,这一次不是沉浸,是回家。我本来就是条鱼,本来不用憋气,但您还是听见了我沉重的呼吸。没关系,涂一些泡沫就好,涂一些泡沫就好。它们覆盖着我的脸,洗尽铅华,露出鳞片。瀑布再次倾泻,我本鲑鱼,逆流而上。腮还没有张开,还好我学会了蛙泳,噗~~~~啊~~~~~噗~~哈~~!
失败了,我尴尬地出水,快速把自己擦干,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定是洗面奶出了问题。这些广告里的泡沫,把毛孔里的尘垢具象化,生命化,火药味的战争,终究是可视化,显微镜的把戏罢了。水中的世界排斥污迹,也稀释声音,可这泡沫除不掉我面上沾染的杂音,水不容我,只好带着一脸油腻的嘈杂,深深陷进枕头。
Mar.23.2013.PM11:05 (洗鼻子)
人鱼传说(下)
怎么能就这样睡去?我又试了一次,深深地呛了水。
不可歌,可泣。
Mar.24.2013.AM10:41 (公园陪孩子玩儿)
礼拜天的上午,全家陪女儿玩。金属的轴承嘎吱作响,这是一个旋转的游艺器械,女儿和保姆就坐在上面,一圈一圈地做离心运动。感觉如何?“晕啦!”女儿喊着,“晕死了~”保姆也喊着。晕就对了,女儿你明白吗,日常生活里我们都不会旋转,旋转的是滚动的皮球,汽车的轮子,而不是我们。正因为如此,你才会觉得好玩,你才会坐到这上面,觉得新鲜,你晕了,却还不能下来,多转几圈,重复,重复,才有效果,才有新的体验,你发现周围的世界模糊,消融,泼洒,变成一锅粥,他们让你看着我,让我拍下你,我做不到,糊了,你看不清楚我,我也一样。你听到风吗?像不像妈妈平时做饭的声音,沸腾了,呼呼的,闻到香味了吗,你饿了吧,再转几圈,你会勇敢,下一次你自己上去,抓着稳定的东西,把自己投入漩涡,打破那些既定的轮廓。
Mar.24.2013.AM11:27 (公园陪孩子)
喝水!啾啾啾啾~~不看着脚底下还不摔你!?啾啾啾啾~过来,喝水!啾啾啾啾~~快两点了~~哇啊哇啊哇啊哇啊~~~嚓嚓~~赶快走吧那就~~~哇啊哇啊啾啾~~~看喜鹊!啾啾~~坐这来!哇啊哇啊哇啊哇啊~~这边也能看到啊~ 哇啊哇啊哇啊哇啊~啾啾
公园里最适合捉迷藏。在大人的喝令下,在鸟鸣的夹缝里,孩子们不见了,他们于远山中喊叫嬉闹,隔着雾,若隐若现,分不清游玩更重要,还是自由更重要,当喝水和观看变成指令,公园只是黑板,谁能在上方的粉笔字里,找出孩子的蛛丝马迹?
Mar.25.2013.PM07:18 (厨房做菜)
有人喜欢黑胶,就喜欢里面沙哑的“炒豆声”,如同阿城说过,好吃的菜,有股“锅气。”
噪音和语言,哪个更有吸引力?为什么此刻我选择远离客厅里妻子和女儿的亲密,而在厨房的油锅边站立?哪个更油腻?是日常的絮语还是锅里的花椒粒?或者前者太索然,所以要借助锅铲,把辣椒煸干,让对话在炝油中浸染。今天的饭菜与往日不同,我把耳朵扔了进去,个别词语有些塞牙,吞咽时候小心有刺。
Mar.25.2013.PM09:41 (深夜安静)
斋戒。
每天可接收的声音是定量的,可制造的声音也是定量的。
维生素。
素食,是种选择。
素色的衣服,简单的款式,舒适的剪裁,对面料的重视,而不再执着于夺目。
炫目=香辣=嘈杂。
我=呼吸=思索=关了的电视。
简朴,量入为出,收着点,节约。
别弄出大动静,少弄出点动静。
Mar.26.2013.AM10:02 (上班同事和小黑上楼?)
散散步,上楼,楼道,楼梯。
我的脚步声略沉,因为背着女儿,妻子拎着车,车轮和楼梯磕磕碰碰。声音是种权利,也是能力,女儿,你感到奇怪吗?爸爸妈妈和刚刚坐在上面的小车,都有上楼的声音,为什么你没有?脚步声(上楼梯的),你渴望它吗?之后你会有多少次上下楼,在夏天的晚上,你能熟悉地分辨每个人的脚步声,你会习以为常的,而有一天它们又变得陌生,当它们包含更多的内容,比如衰老,争吵后的冷战,醉酒,和更多你无法觉察的秘密。无论如何,人们掏出钥匙,打开那扇门,将自己关起来,或者瘫倒在门口,或者踌躇不前,鼻尖渗过门缝。多少相逢,多少独行。爸爸希望你的脚步轻巧,稳健,有人搀扶。
Mar.26.2013.PM02:11 (办公室同事聊天擦东西)
摩擦是种清洁的方式。从橡皮开始,到回家前搓掉手上的泥,用利刃刮掉鱼的鳞片,刷子去除饭锅上的嘎巴儿,揉洗衣服上的油渍……今天下午,有些东西被摩擦掉了,我们悄悄嘀咕着。毕竟不是消除,是排斥,是分离,用撕扯,拥挤,碾磨,每一种听起来都很血腥,却区别不大。有一些暴力在悄悄发生,却可以明目张胆地发声。把在一起的强制分开,嚓嚓,嚓嚓嚓嚓。
Mar.27.2013.PM10:18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都散了吧,这是你们看过的最短的演出,但没有退票,也不是玩你们,再见,再见。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哑巴所不能体会的,他会觉得我在浪费,浪费这种天赋,他在嫉妒我,眼睛都红了,我是如此轻易地放下了武器。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今天”只是个借口,其实你我都清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什么好说的,那即意味着,我没什么对你好说的,你没什么对我好说的。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说”只是个比喻。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我可以一直写下去,这个开头给了我无限的灵感,但是——
今天,没什么好说的。
Mar.28.2013.AM10:26 (街边车流和鸟鸣)
开车驶在城市的边界,耳朵被切成两半,一边是汽车的轰鸣,一边是鸟叫,并不是左右声道的关系,并不是。于是我也开始纳闷,这奇异的景观令人不解,因为它们如此对立,又站在一起,只有一个解释,鸟群已经习惯了这种噪音,车流,听久了,成了瀑布,成了大河的转弯,成了猛烈的风,成了自然——这种意淫蛊惑着我,听得入了迷,忘了分贝测试,忘了噪音标准,对鸟不适用,对我也失了灵。公益广告中孤零零的枯树显得耸人听闻,放心吧,我们都会活下来的,活在新的景观里,那是发动机的郊野,然后一起死去,在最后一声鸟叫之前。
Mar.28.2013.PM08:11 (广场行走)
这旋律来自80年代,或者更早的金色旧时光,它一般出现在夏日夜晚的街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再年轻,腿脚尚且利索,便手挽手,来到小区空地,或市中心的公园,在夜幕中模糊了年龄,翩翩起舞。我推着凤凰自行车,听着墙外的硬底子皮鞋声,推开了铁门。人们依然统一,却不再宏大,向往独立,崇尚个体,我不自觉地跟上了那个女人的背影,用节奏找节奏,脚步声重叠,构成一个最小的集体——只可惜,不出五步,我已经乱了方寸,分道扬镳。也罢,有人留在了上世纪的门口,流连落泪壮烈牺牲,有人成了阻碍,有人成了梯子。带着所有盲目和新鲜,我迈了进去,我拥抱,我伸开双臂,迎向我的舞伴……
Mar.29.2013.PM12:57 (办公室电话狗哼唧)
午休,休息,公司,谈话。Lisa跟电话谈话,我跟狗谈话,这是个姿态,我们都没跟人谈话,午休时间,我们不喜欢跟人谈话。没有侮辱电话那头儿的人的意思,只是在我听来,Lisa的谈话里只有她一个人,而在Lisa听来,我和田园犬小黑的谈话中,只有我一个人。在我们所在的空间里,只有我和Lisa在说话,但我们俩却没有交谈。我在模仿小黑的语言(虽然只是象声),Lisa是听不懂的,而Lisa虽然说的是“人话”,可我就听得懂吗?
小黑叫了一声,隐蔽在我们的“谈话”里,它也觉得荒唐。
Mar.29.2013.PM10:43 (深夜安静电视小声)
妻子陪女儿睡了,我探身起来,轻轻打开电视。欢呼声热烈,微小,我让它微小,再微小也是欢迎,欢迎这个还没睡的人。屏幕里鬼鬼鬼祟祟的聊天,午夜电报的密码,这是重播节目,每三句话的头一个字,就是密码的内容。这种想象并不能让我兴奋,每个晚上,在每个客厅里,都有一个男人独自对着电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还不睡去。他们只是卧在沙发上,黑着灯,电视照着他们没有表情的脸,通常是严肃的,无法从中知悉观看的内容。这是一个最大的秘密组织,他们悄无声息地存活于夜晚的微小的音量,听觉极其灵敏。
Mar.30.2013.PM02:14 (孩子玩儿乐器背景电视)
电视的背景音乐像个童话,可女儿的世界要有想象力的多,她对待乐器的方式像罐头,城堡瞬间耸立,只在咿咦呀呀之间,樯橹灰飞烟灭。论即兴发挥,我跟她差得远,她对结构的把握也是天然,当然,这解读是我的,我用越理性的解读来赞赏她的感性,说明我离感性越远。音乐会听了让人舒服,流眼泪或大汗淋漓,鼓掌,跳水,我喜欢我女儿的日常演出,一次一次地倾听和欣赏,比信仰来得亲切,比逻辑更让我信服。
Mar.30.2013.PM02:16 (陪孩子看书什么是当代艺术)
不得不说我有点偏执,那就是我可以让自己的腔调可爱,但不刻意回避高深也不刻意营造幼齿。就像现在,女儿玩腻了玩具,爬到了我的书架前,顺着她的指点,我把书抽出来,得到她的首肯之后,念给她听。她懂吗?这根本不是问题。当代艺术和品牌中国,也不过是成人世界的玩具,她想玩玩,就给她玩玩,她觉得无趣,就去看电视了。话是这么说,可我为什么要坚持一下,是因为我的玩具受到她的冷遇让我觉得失落,还是她的多变让我不太适应,我是否太过于古板?深刻有时意味着僵死,而我对她的玩具感兴趣吗?我可以陪她玩一下午积木,而真的乐在其中吗?女儿,我对你并不平等啊,有什么权利向你推销呢?
Mar.31.2013.PM04:35 (孩子铃铛围观)
这是个不寻常的下午,全家人围着跳舞的女儿,比舞林争霸隆重多了,她旋转,摇摆,跌跌撞撞,每个动作都拥有欢呼和称赞。我想告诉她,今天她拥有了一件特殊的身份声音标识,那就是挂在她手腕和脚腕上的小铃铛——从此在闭上眼睛的世界里,她即使不咿咦呀呀,也不会被别人听而不见。可能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鲜劲过后,她哭闹起来,这悦耳的颤动是个累赘,贴得太紧,像影子一样甩不掉,姑娘本逍遥,来无影去无踪,你们凭什么把我符号化呀~
Mar.31.2013.PM07:18 (超市买单)
我在横横竖竖中穿行,推着推车,车像张网,我像个渔夫,信手捞一捞,把方便面扔进网里,把果丹皮扔进网里,把抽拉纸巾扔进网里,把生牛肉扔进网里,把一个榴莲扔进网里,把流行歌曲、撞击和杂谈扔进网里。嘀,嘀,嘀,嘀,嘀,嘀……船驶进码头,贴了标签的,被显示名字和价格,没贴标签的,这个收银员看不见,抓不着,但我知道它们就趴在网里,塑料袋是装不下,我自有办法。
Apr.01.2013.AM09:50 (花园小鸭子过来)
小姑娘在岸边
老将军牵着她的手
咳嗽声像打水漂儿
在河面上蹦了三下儿
老将军隶属于海军
指挥一群野鸭,
他声音洪亮,不减当年,
连喊7声,“小鸭子,过来!”
可惜,无鸭响应
这不怪您,爷爷
小姑娘听出了风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把命令吹走了
Blowing in the wind
老将军的名字叫鲍勃迪兰
小姑娘的名字叫刘胡兰
他们站在岸边
野鸭子越游越远
Apr.01.2013.PM09:55 (我今天丢了一段录音)
“我丢了一段录音,今天。”我这是在对谁说?对小老虎说吗?说的意义是什么?他又不是侦探,我的录音又没有落在出租车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苹果手机靠不住吗,还是转进电脑的时候操作有误?这么多天我都没有出过差错,或者出过,但我没说。声音易逝,我用电子网罩套住它,像捉了一只蜻蜓,百密一疏,谁知道它从哪扇窗户钻了出去。“我丢了一段录音,今天。”我对自己说。语调平静,茫然,并不想哭,毕竟那只是一段录音,不是一个钱包,也不是一段爱情——这个推测不准确,我怎么知道那不是呢?我不说,没人知道那段录音是什么,如果我忘了,多年之后,听到这句话,我会抓狂,那段录音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不去描述一下那段录音呢?如何去描述,这是个问题,用时间和地点吗?用拟声词吗?用画面吗?描述有意义吗?如果没有意义,那我和小老虎的这一个月在干什么?“我丢了一段录音,今天”——这本身就是一段新的录音,因为丢失了一段,才拥有了这一段。时间增添了一个新的伤口,旧的是否已经痊愈,我不得而知。
Apr.02.2013.PM06:28 (办公室吸氮气大笑)
太猛了,太猛了!我不吸,我可不吸。怎么猛?不是吸一口,我声音变了,那是物理的小把戏,我是说,这罐子里的气,对气氛的改变太猛了。就这么一口下去,全屋子的人都疯了,由一个人的独奏,到各路大笑齐鸣,空气在剧烈流动,口哨变成了风暴,隐藏的沉默之人也无所遁形,他们的面部肌肉被刺激,胸腔共振,暴露目标——国际法规定,不是禁用这种气体武器了吗,怎么能在办公室随便搞人体实验呢?
Apr.02.2013.PM07:02 (小区健身器吱呀)
视觉成为声音的注脚,我要记一笔。小区健身器的轴承吱呀吱呀,这是缺少润滑油的声音,是生锈的意思,听上去像老迈的关节,通俗惯用的修辞。站在上面的,是什么人,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太多不同,无非是体重和运动幅度的差别。可当一个小女孩站在这老迈的器械上,与傍晚的天空一道,成为这锈迹斑斑的钢铁摩擦声的注脚,我开始警惕视觉文明的干扰,和大众审美的倾向。妈妈,我不玩了。小女孩走了,摆动没有停止,我还得跟自己的标准玩一会儿。
Apr.03.2013.PM07:41 (爷爷奶奶逗孩子)
这不是小红帽的故事吗?小姑娘,外婆,大灰狼,齐了~
Apr.03.2013.PM09:51 (与父母家乡话聊天)
我跟父母讲着方言,我们吞咽,我们咀嚼,这份味道,我多么熟悉,旁人多么诧异。在北京,很少有人听我讲湖南话,相比之下说英语的次数都要频繁得多。陪伴我长大的语言被割掉了,当我决定离开那地方的时候。比肉还要贴身,但不会流血,像个背包,平时往旮旯里一放,落层灰。我的口音听上去有些干瘪,似方便面里的脱水蔬菜,妈妈和爸爸的语气鲜亮,咬字劲道,戏剧感十足。说什么不重要,还好没有关闭通道,当有一天他们走了,我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使用这个频率。语言是工具,越磨越锋利,像我的普通话和英语。口音捆绑着土地和树根,无论我多恐惧,也终将失去现在这安谧气氛,远去了魂。
Apr.04.2013.PM03:25 (下电梯到户外)
刑满释放。
Apr.04.2013.PM04:58 (家里短信)
录音技术是伟大的发明。科技本身即是侦探,侦探最重要的道具是放大镜,放大镜从蛛丝马迹里发现真相,录音技术是镊子,是吸尘器,把头发丝留下来,放进电脑里,再微小的谈话,都可以变成放大的波形。我和我的手机同处谈话的远方,我听得漫不经心,手机忙里偷闲接收了两封信,我问我的手机,他们在说什么呀,我的手机回答不了我,只能一遍一遍重复放给我听。有一个纪录片叫《牛皮》,里面有很多黑黑的镜头,那是导演在夜里拍的,没有光。她告诉观众,“你们看不到的,我当时也看不到。”
Apr.04.2013.PM05:37 (妈妈厨房切菜)
妈妈在切菜,刀落在案板上,不是太响,这代表衰老还是安详,或许只是食材柔软,温柔对待即可。刀侧着切下去,直着切下去,切在不同的纤维上,切在经验里,切中我的要害。在越来越多的瞬间,关于老人的声音,我都会竖起耳朵,它们不像儿时的叫卖般独特,但堪比留念的照片,我一声也不想放过。
Apr.04.2013.PM10:52 (家里深夜电器电流声)
夜晚的安静,让人看到狼的眼睛。将耳朵贴近一些电器,可以听到隆隆的低频。其实它们一直都在,只是白天太亮了,我们需要墨镜。比如冰箱,这种电流经过,内在运行的振动,是它的呼吸,比人类稳定,可靠,单调,无聊。稍走远一点,就听不到了,再贴近,如潮水又没了脚。低频是种治疗,中医推拿耳膜,亦是修行,禅定观自在。这种重复让我舒服,险些拿个枕头过来,靠着冰箱睡了。
Apr.05.2013.PM04:13 (户外风声爆裂)
我拎了一个袋子出门,去采集风声。收获不小,纯度挺高,往滤网上倾倒,留下一些杂质,如下:
孩子的叫声
几句对话
磨刀人手里金属片的撞击
“我能借你手机打一下吗?”
我自己的脚步声
几声鸟叫
车轮碾过地面
“爸爸你……
无声
Apr.05.2013.PM04:18 (户外鸟鸣)
就当我
差点以为这世界上只有鸟和孩子的时候
一声汽车喇叭
把我拉出童话
好想在
鸟与童的王国中
多驻足停留一会儿啊
Apr.06.2013.AM11:19 (动物园风吹落叶)
风吹落叶,脚踩塑料袋,手揉搓玻璃糖纸,小心翼翼。均匀的喧闹围成一个圈,音量整齐,如同被齐刷刷切断的秸秆。标准的电影出场,镜头在背后,瞄准右手和双腿,远景是熙攘的人群,主人公顿了一下,向前走去。
Apr.06.2013.AM11:34 (动物园碰碰车)
碰碰车猛烈摩擦地面,撞击周围,正着开,倒车,四面八方,蹭,撞,孩子喜欢这感觉,我也喜欢,每一次撞击都如同一次开关,我就是订书器,在时间的胶片上扎眼儿,按在钉子上方的手,现在握在方向盘上,告别了这一个月的工序流程,以狂欢结尾。生活继续,继续发声,继续收声,继续活在声音里,继续活在时间中。书写,录制,存档,欺骗,梳理,调戏,自缚,埋伏,旋转,旋转,撞击,欢天喜地,懵懵懂懂。
2022.03.13
2013 “寄生/声”项目 – 声音写作文本 (Zafka)
Mar.06.2013 AM 07:59 (万物皆有声)
生活就是永无间歇的出演。吸气,呼气。但不到紧迫之处,几乎无人知觉。我从不是个好听众。世界太庞杂,这样的清晨太多。仍是母亲的呢喃,或有锅盆碗碟的撞击。震荡的物理波纹,时间被粗鲁的仍在波谷 ,无法动弹,几近停滞。“你说,关键是你不听劝…” 母亲点上烟,叹口气,把盘子放入水池,走了几步,靠近门。我汲着拖鞋,起身跟随母亲。世界在屋外,鸟鸣狗吠,交通往来。我决定就这样开始,以耳为媒,把自己剖开。我感激这一个重复的清晨,它无比清晰的向我告知:时间只是一围静止的湖,纵身入水,跌跌撞撞,万物皆有声。
Mar.06.2013 PM 01:04 (自我复制却从不重复)
让人生厌的上午。跑了一路回家。房间里空无一人。邻居家还在做饭,刀过案板,零零星星。我直直的坐下,开始大声呼吸,没有来由的重复再重复。我痛恨重复。我是一名痛恨却无法摆脱韵脚的MC,以回转的语言技巧,一次一次峰回路转的头尾相逢,赢得人们和自己的安全领地。我痛恨重复。我相信诗性,相信诗性来自无法精确控制的身体,来自身体对未知的容纳。我痛恨重复。此时,我只是想和身体一起呼吸,并在午夜聆这些被抽离的重复。因为这是绝妙的艺术。呼吸是自然的造化,它自我复制,生生不息,却从不重复。
Mar.07.2013 AM 01:03 (声响巨细)
凌晨。胡同里的这间租来的小屋,我独居。打开灯,轻走三步靠窗。偌大的北京,便在这持续旋转的光圈里,无限缓冲。安身,安声,安生,安心。沉静的布匹,安歇的机器,窗外笼里睡梦中的鸽群,在黑夜里持续低声嘶鸣。上三寸,下两分。每一种声响,皆有巨细。每一次细微,都换来我与世界之间,深不见底的沟壑。每一次细微,皆是安神。
Mar.07.2013 AM 11:42 (房间剥离了语词)
中午。锅。铁锅。金属。水滴。点火。火焰。吞噬。空气。干裂。风铃。嘎然。短消息。手机。拖鞋。小跑。噼啪。噼啪。小火。灶台。火焰。燃烧。空气。锅。铁锅。金属。水滴。点火。火焰。吞噬。空气。干裂。风铃。嘎然。短消息。手机。拖鞋。小跑。噼啪。噼啪。小火。灶台。火焰。燃烧。空气。锅。铁锅。金属。水滴。点火。火焰。吞噬。空气。干裂。风铃。嘎然。短消息。手机。拖鞋。小跑。噼啪。噼啪。小火。灶台。火焰。燃烧。空气。锅。铁锅。金属。水滴。点火。火焰。吞噬。空气。干裂。风铃。嘎然。短消息。手机。拖鞋。小跑。噼啪。噼啪。小火。灶台。火焰。燃烧。空气。锅。铁锅。金属。水滴。点火。火焰。吞噬。空气。干裂。风铃。嘎然。短消息。手机。拖鞋。小跑。噼啪。噼啪。小火。灶台。火焰。燃烧。空气。中午。
Mar.08.2013 PM 01:47 (与万物对话但从不狩猎)
绷紧,捆扎,挤压,形塑。包裹。再换个时刻,换些人,用更多的心机和力气,剪开,撕毁,露出,呈现。午后一点四十七分,又一件事物在临界状态。无人言语,屏息静气。放下剪刀,仿似得胜的猎手,在五百平米的空旷荒地,捕捉到一只粗壮的青蛙。你看,每一天,世界万物就这样被传递,速度飞快。胶带和塑料外壳,是你我的忠实掮客,有最简单的统一语言:辞藻尖锐,语法刚劲,音调干燥。我想做个旁观者。我是MC,只与万物对话,从不狩猎。
Mar.08.2013 PM 01:51 (物件是生活的真相)
“打!”父亲发狠。母亲呵呵一笑。“不够长度啊!这太短了这个,够不着啊!” 一把钻孔枪,三颗螺丝,满地零碎的物件。四分钟之前,父母开了个包裹。我在一旁,没打算伸手,也没打算张口。不是语言,物件才是生活的真相。钻孔枪,铁质螺丝,木头部件,泡沫板,塑料袋,它们尾随在父母的言语中。生活的真相,在于我过往听不见,不愿听的物件之间的频密对话。
Mar.08.2013 PM 04:09 (电梯是沉默的天梯)
已经很久没有去上班。成天晃荡在胡同独自租住的小屋,或是父母的住处,偶尔因为接洽零碎的商业活,我才会出没在写字楼。住宅,商场,或是写字楼的底层,都是些尴尬的场所。液晶屏幕的广告,耳畔的私人对话,忽远忽近,粗暴无趣。它们临时,过度。阻缓点时间,囤积点时间,释放点时间,是这里的唯一功能。我与陌生人一起,在电梯前等待拯救的铃声。单音拖着长长的泛音。泛音,即梵音,干净的召唤信号,对当下时间的暂时破除。这是狭窄的朝圣之旅,人们在电梯里谨小慎微,祈祷各自的归属。走出电梯,八层的走道里,只有衣服和鞋子摩擦的声音。我从未去过城市高楼的最高层。这些地方,通常会被人包下来,价格昂贵。我很好奇,究竟是些怎样的对话,值得挑选距离云端最近的房间。
Mar.09.2013 PM 01:51 (饭馆里语言密谋)
在小饭馆儿,跟一位叔叔吃饭。饭馆狭窄。我们的桌子紧靠着门口敞开的厨房。灶台焰火持续轰鸣,锅盆碗碟不绝于耳。叔叔说,聊聊,聊。生意。公司。做主。广告。传媒。本事。说唱。政府。年轻人。叔叔语气平和,不愠不火。我极力的想投入,听着没有说话,却不由自主的往后往身后厨房靠了靠。相比于清脆起伏的锅盆碗碟声,我怀疑一个并无恶意的中年人嘴里延绵不绝的语词。此刻,我还是喜欢厨房的声响。这是些干净,没有规律,赤裸裸的响动。它们有清晰的尺度。它们声声入耳,朴实得劲。人们不害怕物件赤裸的响动,却害怕语词持续的温和。
Mar.09.2013 PM 03:13 (F—–low的方式)
仍然是关于语词。午饭时碰到的叔叔,是朋友录音棚的幕后金主。回到棚里,我斜躺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朋友点了支烟,一遍一遍听刚录制的MC人声部分。自然。城市。选择。爱。力量。力量。爱。混。街头。拳头。自由。根儿。地下。灵魂。止血。世界。伤疤。我突然咳嗽了一声,突然觉得荒谬得紧。摇摇晃晃。语言的韵律是什么?词语的颠倒,重复,反复。停。停。歇。歇。F—low。F——low。语言的河流。无处落地的词。如何才能拥有力量?我不相信诉说,我选择讲述。讲述,是展开,繁衍,茂盛,延绵不绝。在时间上,它不向前,不停顿,也不后退。它只是舒畅的延展。或是戛然而止,或是悄然而至。嘻哈来自敞开的街头,而不是录音棚。录音棚也就是个屠宰场。这些声音,在光鲜的写字楼里被剥掉,一拍一声的修饰,去尘抹土的洗净。或可呈现一张毛皮,但从不是一次攻击。
Mar.10.2013 AM 08:45 (蜂巢般的球场)
约好了朋友周日一早打球。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好习惯。下了车,过了马路,往正南大概走十来步便到了门口,绕过半掩的大门,身后的交通声流沙般不着痕迹的消失。过道里悬挂公共音响,常年播放不着调的轻音乐,或是吉他,或是琵琶。左拐快走,大概三十来步,便可穿过这糟心的声场,甩得干干净净。再顺着球场边,往北一直往前,走不了几步,就能听到球敲击地板,朋友们已经在热身。硕大的室内球场,像个蜂巢,每群人都有自己的孔洞。这共享的空间,看似自由空旷,最终也只是些自我殖民和奴役的声场。人们近亲繁殖,封疆守土,转瞬即逝。虽是一个球场之下,这周日清晨,满球场打球之人,未曾有面红耳赤的相互聆听,更谈不上冲破领地的暴力对话。
Mar.10.2013 AM 09:48 (模糊私人化记忆)
什么是私人声响?我坐在球场边,汗流浃背。朋友们还在场上争斗,跑动,发球,投篮,叫喊,鼓掌,争论,唏嘘。这是熟悉的声响场景。你可以从街头任何一个球场,甚至电视里听到它。此时,恍惚之间我不知身处何处。很难说,这是3月10号早晨9:48分,我清晰可见的一段私人声响记忆。什么是通往私人声响的密码?是因为没有例外?是因为只有例外造成的陌生,模糊和稀少,才能从重复发生而得以教授,并习以为常的声响密码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没有标志性的声响?是因为如同一张景物照,拍摄者没有出现在场景之内?
Mar.10.2013 PM 01:09 (风是广场的保洁员)
打完篮球,往北走到天安门广场,准备去坐地铁。来自各地的旅游团,操着不同的方言,或稀松或紧凑的游荡,声音弥散在广场。我是北京人。在这广场,我也是个外地人。我停下来,混在一群叔叔阿姨里,顺着导游的手指,一路听过去。导游随身带着小喇叭,声气充沛,指出圆形的国家大剧院花了八十个亿。有叔叔细声问,进去看要钱不?导游说,那里有朗朗和宋祖英的演出,票价要两三千。但是这很平常。因为父母会带孩子来看演出,为了学音乐。在另一边,方形的建筑叫公安部。天圆地方,一文一武。一东一西。叔叔阿姨,这就是北京,大家现在去卫生间吧。叔叔阿姨有些犹豫,还在盯着导游嘴边的小喇叭,看看卫生间的方向,看看小喇叭。这是他们和这个城市合法的接口,一旦放下,他们便和这里没了干系,嘭的一下四处散开。我离开的时候,广场一直在刮风。有风的地方,声音容易传开,但什么都不容易留下。风,是公共空间的最佳保洁员,也是隐秘广场的真实身份,广场历史的统一注脚。
Mar.11.2013 PM 12:09 (公交里的毛线团)
出门。坐了趟公交。车里人不算多。坐的站的,身边七八号人。他们交错着面对面,持续说话。有本地口音,也有外地口音。听起来,情绪都不错。模模糊糊。我坐在其中,耳边像是缠了一团毛线,柔和,不扎手,但也基本没有头绪。这意思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念头刚冒出来,已经被吸了进去。我就这样坐了一路,眯着眼。窗外阳光很好,公交车的轰鸣没有断过,都来的真切。
Mar.11.2013 PM 01:04 (餐馆儿的马帮)
一路公交坐下来,倒是饿了。在爷爷奶奶家附近的街边,找了个馆子吃面。正前方那桌的两个中年女人,在谈论支票,毛利率和投资,家族生意和市场。声音不大,不骄傲也不着急,就像讨论点买菜做饭的家常事儿。馆子里电视机挂在身后屋角,听不太清楚,是些喃喃自语的日文流行歌曲。餐馆是城市里人们钟爱的剧场。人们来这儿聚集,以座椅为单位,讲述故事,交替出演。座椅之间相互窥探复制,再杂交和繁殖一些新的,就在一碗面的功夫。馆子里的电视,是有趣的装置,这是一个接口,一段界面,一种呈现。这些逃逸至此的食客们,抬头便知,馆子小剧场演绎的,和这电视里的世界相比,可能被瞬间淹没。我喜欢独自在餐馆进食。我是一个MC,讲故事,也四处收集故事。女人们讲故事,我大口的咀嚼,喝汤。磁的碗,瓷的勺,木的筷子。瓷勺敲击碗边,仿似马帮的马匹,在休息的中道食草饮水,饥不择食,脖子下的铃铛不断作响。我喝了口手里剩下的矿泉水,漱了漱口,吐在剩下的面汤里,砸出了一点浪花。
Mar.11.2013 PM 01:12 (糕点店与缠绕的对话)
吃了面,上楼爷爷奶奶家之前,照例去了趟楼下的副食品商店。这是家北京老店,卖各种老式糕点。爷爷奶奶喜欢吃。站在柜台前,我很享用说出这些语词:半斤杏绒饼干,白萨其马,半斤拿破仑,半斤枣糕,半斤豆沙方饼,两块金珠饼。我是个北京孩子。这些食物的名称,加上斤两,说出来,只要说出来,就是随时给了自己一些舒坦的理由。糕点放在电子称上,包装纸脆脆的。年轻女售货员的声音,也脆脆的。她们的外地口音啊。女售货员对着女售货员说,昨晚做了个梦。中了五百万,挺邪乎的。去韩国了。妈哟!他们家特豪华,请我吃韩国泡菜泡饭。这几天老做梦。转身看我的时候,女售货员也问我,白馅红馅?半斤枣泥?还有啥?女售货员也回答我,金珠饼里,加的是南瓜。这是些缠绕的对话。女售货员是糕点的牧羊人,她和另一个远方的自己对话。我是遗失的权杖,我和身后的自己对话。其实,我们说话,但很少对话。这些语句,就在空气里穿行,光溜溜的,没什么交情。刚好五十五。来个塑料袋吗?
Mar.12.2013 PM 02:54 (手机亲近音箱)
滋滋滋滋滋滋滋iziziziziziziziziiziziziziz……….手机亲近音箱。这些天,我一直沉默寡言。我有了更多的兴趣,聆听万物的声音。我想让音箱说话。手机想跟音箱说话。我没有开口,但音响反映强烈。稳定的频率和速率,持续不间断,如同手持一柄光剑。万物皆有声。物件之间的对话,是公开但无人倾听的密语。对人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种干扰。我可以打断它们的对话。听我说。我是MC,开口时,音箱才开始说话。何谓与万物对话?听,他们与你对话。
Mar.12.2013 PM 08:46 (卫生间虚掩身体与水流)
端坐。卫生间的时光,一定会慢些。门就虚掩着。隔着门,我听见,客厅里父母在看电视。电视里在放京剧。也许他们没有看。我又听了会儿。恩,这是三个空间。从电视机,到客厅,到卫生间。我们仍然悬挂在这个世界里,丝毫没有脱节。电视传送外部世界的声音。它生长在客厅里,开开关关,播播停停。这些响动,便是家庭的生命之树/指数。很多时候,客厅再大,父母也不太说话。我也懒得说。聆听彼此太累。电视才是传教士。它不知疲倦的陪伴。我们听电视机的。而卫生间,它狭小,少有回声。不需要对话,只需要关注身体与水流。不客气的说,抽水马桶才是家庭的教堂。每一次冲刷,大抵都是这新世界抵达的福音吧。恩。起身,冲掉吧!师兄啊!!!
Mar.13.2013 PM 12:27 (摩擦金属部件的游戏)
中午时分,下楼找个地方吃饭。穿过院子里的户外全民健身器材区,附近工作的年人趁着午休时间,三三两两围聚在不同的器械前。这些金属器械,常年经受风吹日晒,皮肤斑驳,骨节生涩。金属部件之间,嘎吱嘎吱,重复摩擦的高频,赶得上小鸟的叫唤。还有金属转筒履带的跑步机,走上一步,便持续在沙沙作响。无需抬头,你还能听到乌鸦们在交通声的上层,在树端,愉快的鸣叫。对于附近的年轻人来说,这儿是他们的公共空间。固定的金属健身器件,是社交的优良工具。身边的年轻情侣在器械上较劲儿,可以躺下去,但是能完全躺下去吗?哪有什么健身,都是些甜蜜的嬉戏。
Mar.13.2013 PM 12:37 (拔河与123)
不到十分钟光景,这些在健身器材区闲散的年轻人,已经重新组织起来,开始了一场拔河。我晒着太阳,站在一旁,静观。拔河是人类原始竞争形态的一种保留。准备好了吗?绳子绷得直直。人们反复研究节奏,身体,气息和力量的关系。加油,加油,加油,观战的女孩子嗓音又高又亮,急切稍显凌乱。一二,一二,一二。参战的男孩子以中低音有节奏的呼应和调整。风很大,双方声音相互压制,忽高忽低。这不是力量的简单对抗,而是声响的正面较量。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干扰,快速建立和驯服自己队伍的声响节奏,呼应协调身体,最大程度释放力量,才有可能获胜。通常,这样竭斯底里的战斗坚持不了多久。裁判铝制哨子的短促哨音,可以轻易打开水闸,让有组织的紧张声响,一下子松散下来。拔河,直接铺面而来的声响,比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机械的对话来得过瘾,它们像一朵朵就地展开的蘑菇云,开始和结束,都没什么征兆。
Mar.13.2013. PM 06:16 (长坂坡的风声)
究竟什么是街头?土地与风。精致的,静止的,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下楼,出门,从安静的楼道里冲出来,只要几步就是喧闹的街道。我把手里的长板扔到地上,蹬上几脚。哒哒哒嗒嗒嗒,橡胶的轮子,开始摩擦过坑洼的水泥地面,就这样开始滑行。街头不是关于空间,而是关于时间。是每一次与土地和风的接触,是每一次摩擦掉的橡胶,毛发,皮肤,尊严。是睁不开的眼睛。是裸露。是在混杂的世界里,直接穿行,罔顾四周的勇气。站在长板上,我听不清自己的呼吸。只有把速度加起来,你才能听到风声,来自都市丛林的回响。
Mar.14.2013 PM 07:26 (戏剧是对话的结构)
受老储邀请,去看朋友主演的话剧。离开场还有几分钟,场外门厅里播了些funky的音乐。我和老储在音乐里聊天候场。碰到一个姑娘。我和老储在新加坡演出时碰到的姑娘。你,第一天来看这个吗?哦。噢!你,你是前两天刚来的是吗?我昨天刚来。昨天刚来。你记得我啊?当然当然。你那个,腰好了吗?还可以。你是知道我来了,还是?跟我提过你要来。对。但不知道今天,还,还挺巧。昨天晚上刚下飞机,哦,今天就来看了。呆几天?星期天走。星期天走,那还,那还行,呆两三天。我时常陷入这样的场景。这些对话,总是在一些临时缓冲的场合下发生。它们无关紧要,但总会发生。它们看似随即,其实有隐藏的规则。重要的不是声响,而是对话的结构。所谓戏剧,也就是对这些结构的打磨,并且反复播放。在剧场外的门厅,录下来的,就是戏剧。
Mar.14.2013 PM 07:30 (大钟不在剧场)
7点30分。钟声准点响起。这是剧场的开场声。剧场里并没有大钟。钟声录制于寺庙,也许录制于城市高处报时的钟。这是一种声响的戒律,以声响的硕大来表达,以强制的听见来实施。钟声,让剧场黑暗中的人,安静下来,退却下来,肃穆起来,把舞台的空间留出来。如同一道洪水,冲刷走各种私语的灌木丛,让声音退场,让聆听登场。我们共享同一个空间。界定观众与演员的,舞台和舞台之外的,是谁的声响属于故事的一部分。很显然,舞台之外,没有其他声响的空间。正式开演之前,钟声响起之时,观众们只有迅速的咳嗽,清嗓,做一些自我清洁。这里唯一允许的,是在舞台空隙的留白,贡献些沉默,掌声和笑声。剧场是都市中的寺院,钟声是清晰的戒律。观众就是信徒,跟随,默念,揣摩,观望,人们期待神迹。前年夏天,我出演过几场话剧。我明白,只有观众的静默与聆听,才有神迹的舞台。开场的钟声,是驯服的开始。
Mar.14.2013 PM 07:33 (聆听与凝视)
开场三分钟。我坐在观众席看戏。不管台上出演什么,剧场是我能认真聆听的少数空间。戏剧的舞台,它以黑盒子的形态,抽离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它让日常得以被关注,所有的声响都被放大和聚焦。形体动作的缓急,呼吸的快慢,嗓音的质感,对白的间隔,物体掉落的轻重。所谓舞台上的神迹,就是把有些东西抽出来,干净的呈现出来。先生,玩玩吗?先生,玩玩吗?东区最低价。不玩儿?不玩儿?拉到!玩儿,玩儿,玩儿。你抽一口。每字每句,都格外筋斗。对我来说,这样的聆听和凝视,是一种廉价的自我满足。我躲在黑暗和静默之中,舞台于我近在咫尺,分野清晰。舞台与自我保持安全的距离,它试图以神迹捕获自我。但在剧场之外,每一分钟真实的生活,我都是演员和观众。难以分身,更难以确定,哪里是可以容身的黑暗之处,哪里有清晰的钟声,哪里可以自我观望。
Mar.15.2013 AM 12:40 (酒桌上的真戏)
看完戏,跟朋友们去吃饭。喝了点酒。转眼就凌晨。不大的桌子。还是那样,大伙儿交替着掏心窝子说话。都是在新加坡演出时结识的朋友。这样的酒局我常参加。这会儿的戏,才是真戏。刀刀见血。我这个观众,终于可以离开黑暗的观众席,坐在了舞台中央。跟几小时前结束的剧场不同,这饭桌之上,同一时间里,正在同时上演两出戏。一出是男欢女爱,独白。一出是业内情仇,四人出演。酒精让时间缓慢,放大了情绪和对话。就这么盘根错节,我两边都听着。什么也没耽误。左边:她自己牛逼。在所有的讨论会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牛逼。不是,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有人认这个人,知道吗。不是,不光一人认,最重要的是,他妈的这孙子一出去忽悠,他真能忽悠。因为,他们就是说,外国的东西牛逼了,中国的我们看不上。不,蓝蓝,这个思维…咱们单位真的比上海话剧院牛逼啊。不,你不能把这两个一块儿比。虽然…但是…哎,上海戏剧学院的舞美系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是没法弄的。但是戏来说的话,不是舞美第一嘛!上海就是小家子气啊!右边:见着了也没那么兴奋。不知道为什么,而是,觉得一切有点奇妙。当时在新加坡,那几个月,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你存在。我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特他妈的怪,就那么一拧巴。你说我能跟她结婚吗?真不知道。你说我能真移民新加坡吗?也不一定。她的性格我其实真不了解。单纯倒好。到这儿一见到所有人她会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在新加坡租了一房,房东的女儿说特别不喜欢她。搬家了。我草。
Mar.15.2013 PM 07:13 (电影院里眼睛快过耳朵)
电影刚开场不久,全场安静得紧。我并不清楚片中喃喃自语的男人,在讲什么。极重的英文口音。背景的声响,是节奏稳定的心跳,逐步增加音量的合成器黑暗音色,又似涨潮的潮水,在接近脚脖子的一刻,退了下来。这些太费脑子。我盯着字幕,试图跟上闪烁的经过翻译的语义。这确实是看电影,他们说了什么并不打紧,关键是我看见了什么,而不是听到了什么。我的眼睛比我的耳朵快,懂事儿。我能做的,就是摸索着吃点爆米花,咀嚼磨牙,听口腔的嘎吱回响,塑料袋的窸窣作响。
Mar.16.2013 AM 10:47 (绿树红墙吹嘘碧空千里)
恩,这是美好的周末上午。我汲着拖鞋,站在客厅的窗口。我在心理默念。又问自己:凭什么,这么快的,认定这是美好。是歌声吗?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面,迎面吹来凉爽的风。绿树红墙。是黑白的影像,柳树下红领巾孩子划桨而过。是母亲在唱着歌,放下马桶圈,马桶盖,从卫生间开始,满屋子收拾。母亲的嗓音,出奇的清脆,没有丁点犹豫,像夏季林间的水流,浸润了房间。这是周末,城市安歇,屋外鸟鸣,空气轻盈。屋内,人们空了下来。所谓家务劳动,听起来是说:来来,先不要吹嘘碧空千里,与万物对话。先看看家里这些日常之物,它们需要抚慰,接触。
Mar.16.2013 PM 05:56 (俄罗斯套娃不是重复)
我在手机上播放这段录音,同时再次用手机转录。现在,我开始聆听这段新的录音。完美,还是1分17秒。稍微音质薄了些,几乎听不出来。唯一更改的,是手机上显示的录音时间。还是这段声音。在刚才那一刻,我聆听过的那一刻,同样的内容,重新获得了意义。声音,在反复的聆听中获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这是我们录制声音的意义。关键不是重复,重建。而是介入,再造,干扰,实时。通过声音写作重建的,不是以孔窥豹的世界。应该这么说,无所谓重建,我聆听的当下,即时当下真实的现实。把声音录下来,播放出来,让它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对过往的纪念和重新想象。最为吊诡的是,这段声音,是Zafka在饭馆儿讲述关于自己关于声音的过往,而在某一天,他也会仔细聆听这段声音。Zafka是个极爱说话的家伙。我很怀疑,他的整个世界,在一句接一句密集毫无停顿的的话语里,密密匝匝。
Mar.16.2013 PM 11:57 (黑暗的行者在天桥底下)
操!牛逼啊!真正黑暗中的行者!你丫慢点!我看着我的兄弟大卫,在午夜黑暗的天桥底下跳上长板,远远滑开。跟着滑开的,还有我的声音,在天桥底晃荡开。我紧追了过去。我草,你他妈的太凶了。天桥底两侧走道的中部,声音要实在些。魔妖畜生你这是。跳上去,跳上去。走啦!车车车车车车。没事儿,踏踏实实玩儿,玩儿不就是为了躁嘛。小心车,起来。我操,还挺疼。稳住稳住。来,示范!只有空洞的房屋,闲置的厂房,高耸的教堂,冗长的医院走道,封顶的室内球馆,才会有回声,声音才能飘起来。人们喜欢让声音落在实处,易于消逝。在没有光的时间,所有的回声,都是声音记录下的自我投影。这些城市肌体里的空洞之处,风呼啸而过。我们钟情于这些飘荡的空间,它让人踏实。
Mar.17.2013 AM 09:26 (马桶冲走电视国学的尊严)
周日一早,母亲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起床,穿过客厅。电视里,年轻男主持款款而谈。大师刚宣讲完国学。男主持谄媚,盛赞国学妙用无穷,建议一无所有稚嫩迷茫的年轻人,从国学中寻找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声音让我呕吐。不,不,不是声音的问题。他的嗓音柔和,普通话也算得上标准,我听到过太多类似的声音。让人呕吐的,是讲述的内容,话语的语义。可是从我听到的那刻起,这个声音和语义,不由分说,已经生长在一起了。注意,是语义,而不是声音本身,成为了这个声音的个体标签,区隔符号。我忍不住咳嗽,转身往卫生间的洗手池里吐痰,打开水龙头冲走。还不甘心,我又按下抽水马桶冲水。我想用一些新的声音,盖住这个声音。只是简单的盖住,不用争论辩驳。我所讨厌的,就是这个声音。不,不,不是简单的用了一些新的声音。我在征用新的声音背后未曾言说的语义,去对抗我所不喜的语义。让我们在梳理一下周日清晨的声音事件:这不是关于男主持的声音被我咳嗽吐痰加马桶冲水的声音掩盖,而是一段语义被另一段语义所反抗。来,再进一步,让我把这个声音抄写转为文字,去掉声音留下文本,让语义直接呈现,让对抗继续:…受益匪浅。但更多的感受,我觉得,您是在倡导我们,倡导更多人,坚持,修正,或者是努力去寻找一种信仰。国学的信仰。我接触了一些年轻人,也接触了一些成年人,也有一些年长的老者。通过您的国学,我对三种人略微有点感知。年轻人需要国学,因为初出校门,初出茅庐,他们不太容易找到方向。他们需要国学,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该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Mar.17.2013 AM 11:26 (婚礼上的逃婚曲)
周日正午,婚宴的标准时光。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对我来说,所有的婚礼,都是一出喜剧。舞台上,爱情的神圣和家庭的世俗试图达成和解。舞台下,我和朋友们围坐一桌,插科打诨,试图和社会系统的和谐保持适度的距离,以免过度无趣。我也做过朋友婚礼的司仪。不是个好混的活儿。婚礼司仪,不是牧师,也不是红娘,更不是长辈。通常是个没啥干系的第三者。婚礼开始,新娘入场。司仪的角色是讲述,仿佛现场的观众都是盲人,仿佛他是新郎新娘自己人。他介绍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新郎的心情很期待,新娘正幸福入场,身穿洁白的婚纱,在父亲的陪同下缓缓走来。现场音乐响起。太缺了。毕业生的主题曲,逃婚的歌。我和朋友们大笑起来。这几年参加婚宴,见识过从民乐到摇滚乐,从方言到鸟语的各式背景音乐。不管哪种,只要喜庆,舒缓,都影响不了舞台上的表演。仪式还在继续。新娘父亲说,今天开始,我女儿交给你,请你一定要好好对她,你能,做到吗?新郎说,您放心吧,一定能做到。奇妙的时刻,上一辈磕巴的南方话,和新一辈的北方话,毫无障碍的愉快议和了。太缺了。
Mar.18.2013 AM 09:31 (声音是物件之于世界的关系)
隔壁在装修。中低频的机器马达转速柔和。轻触,旋即离开,再轻触,不着痕迹的打磨掉某些物件的边缘,去掉些棱角。晨光中灰尘扬起,不哀不怨。还未停顿,锤子随即跟上,旁敲侧击。这是一场先锋爵士演出的前五分钟。铜管羞涩,无调性的即兴尝试,打击乐见缝插针。这东西让我着迷。每个物件,都有自己的Flow,所谓韵律。物件打开,发声,开嗓。声音并不居住在物件内部。声音,是物件之于世界的关系。
Mar.18.2013 PM 08:17 (乒乓的乒乓)
乓乒 乒乒乓 乓 乓乒乓 乓乒乒 乒乒乓乓乓 乒乒 乒 乒乓乓 乒乓乓乒乒乓 乓 乒乒 乓 乓 乓乓乓乓乓 乓乓乓 乓乓 乒 乓乒乒 乓乒乓乓乓乓乒 乒乒乒 乒 乓乓乒乒 乓乓乒 乓乒乒 乒乒乒 乒乒 乒乓乒乒乒 乓乒 乒乒 乓乒乒乓 乒乒乓 乒乒乒 乒 乓 乓 乓乒 乒乒 乒乓 乓乒乒乒乒乒 乓乒 乒乒乓 乓 乓乒乓 乓乒乒 乒乒乓乓乓 乒乒 乒 乒乓 乓 乒乓 乓乒乒乓 乓 乒乒 乓 乓 乓乓 乓乓乓 乓乓乓 乓乓 乒 乓乒乒 乓乒乓乓 乓乓乒乒乒乒 乒 乓乓乒乒 乓乓乒 乓乒乒乒乒乒 乒乒 乒乓乒乒乒 乓乒 乒乒乓乒乒乓 乒乒乓 乒乒乒 乒 乓 乓 乓乒 乒乒 乒乓 乓乒 乒乒乒乒 乒 乓乓乒 乓乒乒 乒乒乒 乒乒 乒乓乒乒乒 乓乒 乒乒 乓乒乒乓 乒乒乓 乒乒乒 乒 乓 乓 乓乒 乒乒 乒乓 乓乒乒乒乒乒 乓乒 乒乒乓 乓 乓乒乓 乓乒乒 乒乒乓乓乓 乒乒 乒 乒乓 乓 乒乓 乓乒乒乓 乓 乒乒 乓 乓 乓乓
Mar.19.2013 AM 09:18 (会议上的公共与私密)
集团内部杂志编辑兼记者。我早已辞去这份全职工作,但得空还在兼职帮引我入门的杂志社老领导做事。今天是一整天的集团会议。台上集团领导在讲话,呼吁大家去看哈佛商业评论新一期的专题:传统广告已死。声音通过麦克风和喇叭传过来,在会场里飘荡,四面八方。我在台下坐着,用笔在纸上戳,划,写,涂。我在记录,为刚确定好的选题。这些会场上的话语,它逐步与发言者脱离,把自己抽象成一个事件,一个巨大的有机生物。沉默者聆听它,被它笼罩。坐在一旁,我的老编辑扭头轻声告诉我,台上这人嘴里讲的这些,无所谓。你跑一趟。去19楼,要一本新的财经杂志。找到他新写的文章看看。老编辑的声音就在耳边,非常实在。有些东西破掉了。舞台之上,麦克风和音响,再大的场面,再大的音量,也抵挡不过一次简单的交头接耳,一捅即破。
Mar.19.2013 PM 05:18 (非会议的会议与话语的霸权)
会议持续了一天。不长也不短。会刚结束,老领导带着我半道截住集团的领导老范。还是为了这期内刊的稿子。我想问有关会议形的问题。老领导说,是个好问题,但你不能在会场提问,身份不合适。现在行,会结束了。这期就这么一个采访,让老范谈谈这次的会议形式。老范对我说,建议你去查查。Unconference。有报道标题说,24小时神经质。我“哦”了一声。我们三个就这么站着,短暂的两分钟。是否也算得上一个新的会议?人是最大的发生机器。从说话开始。言语,透过不同的躯体和大脑,生长起来。成为一些景观,或近或远。成为一些钥匙,打开或者关上。成为一些气泡,升起来或者落下去。会议,是对人类聆听模式的终极挑战。它是景观,是钥匙,是气泡。如何在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建立相互聆听的模式,让言语有序?听不见。没听见。听不到。诸如此类种种。失控才是会议的常态。你相信unconference吗?在这里,无序才是真正的秩序。如有沉默,是等待还是屈服,还是根本无意?此刻,我最常说的一句,“哦”!“恩”!
Mar.20.2013 AM 11:09 (机场的仁慈)
飞去上海演出,更是为了见女朋友。上午的班机,正在安检。手机。硬币。雨伞。登机牌。iPad。相机。电脑。外套。裤兜。把物件和身体分开,但又把身体物件化。一左一右,穿过机器,被射线看穿。金属物件不说话。我也无话可说。滴~~滴~~~。长声或者短声。单音节是最高效的警示声响。安检,就是些命令。提示。检查。检视。让物件曝光,剔除不需要的杂质。安检,没有人检查大脑的金属质地。我同iPhone交换了耳朵。你所听到的,只是我的iPhone所听到的。它先站在我的手里,又顺利躺在塑料筐里。被盖住。它滑上了传送带,穿过扫描机器的隧洞,被看不见的射线共振。随即又被扔出来。它像一个导盲犬,带我进入看不见,也听不到的机器内部。安检,是等待被看见的过程。所有的看见,开始于听见。我们聆听指令,聆听警示,它们来自机器和身体。我们服从声音,随遇而安。
Mar.20.2013 PM 03:51 (地铁里重复时间的乞讨者)
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包括你我在内,这个世界的声响景观,大抵来说,可以机械的理解为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无数个不同长度的声音景观,各自不断重复,相互嵌套在一起。地铁的关门,启动,加速,减速,刹车,开门,2到3分钟重复一次。地铁车厢里的电视节目,也许每3小时重复播出一次。年幼的乞讨者,抖动手中堆积硬币的塑料碗,5秒钟重复一次。他嘴里的乞讨词,5秒钟重复一次。重复,只是现代时间概念下,都市景观不可避免的内在骨架。这没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世界的趣味,在于错误,每一次重复的些许差池。世界的趣味,更在于我的双耳双脚,所选择的与某一位重复者的距离。下午三点五十一分,我所听到的世界,就在每一个循环错节的点上,与众不同。
Mar.21.2013 PM 09:04 (街头与拟声的身体)
还在上海。和女友从家里出来,去演出场地。我没有和女友说话。高跟鞋敲过人行道。汽车呼啸而过。这是午夜爵士说唱演出的预演。我即兴哼,女友即兴回应。感觉极美妙。不是语言,也不全是乐音。它臣服于情绪,发乎于身体。身体难得自由。张嘴,却不给指引,发声便成了极难之事。人们需要结构。所谓拟声,模拟声音。人学习如何说话,如何奏出乐音。人被语言控制。从身体到心灵。即兴的语言太少。即兴的非语言更少。我们需要一些新元素,没有结构,就来自即兴的瞬间。在街头,相互激发,只需几个来回。这种交流,不同于现场的乐音,也不同于我擅长的即兴说唱。它直探身体和情绪的柔弱之处,羞涩,不知所终。即兴让人不适,它试图借助于记忆。记忆闪断,模糊,人忽然柔弱起来,害怕没了章法。剩下女友的娇嗔之声,在这一段胡乱的即兴里,情真意切,稳稳当当。
Mar.21.2013 PM 09:10 (出租车上的丛林雨蛙)
一把上好的刮胡刀,必是一只上好的丛林雨蛙。半个月过去了,我的耳朵对世界敞开,世界也对我敞开。我并不太明白,这些丰富性,重复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在意。现在,坐在出租车里,等待红灯的片刻,师傅在刮胡子,世界停滞。女友在一旁说,我们不在出租车里。我说说话,我们就在火车里了。我只有在坐火车的时候,才会特别注意声音。也许是因为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不,不,我们不在刚才的火车里。我们在豆瓣里某个故事的火车里,什么火车我都愿意坐。我们在豆瓣故事里主人公搬家的旅行箱里,塞满了一辆金杯。不,不,不,我们也不在别人的行李箱里。这次搬家,我没有拉杆箱,我把行李寄走了。也许,还是通过火车。还有什么区别?我问。你看,没什么区别。出租车还停着,只有语言才能超越空间,或者,在空间之内繁衍空间。双耳封蜡,止于幻听。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把自己给丢了。
Mar.21.2013 PM 12:50 (风和日丽的宇宙)
这是道谜题。一声一宇宙,层层叠叠。我猜想,当自己发声之时,我是否在自己试图录制的声音宇宙之内?如果在,我又在宇宙何处?让我细细数来:第一层。风和日丽。第二层。窗外的打桩机,突突突突突突的吐着信,侵入地面。第三层,我在高楼屋内,斜坐在电脑前。第四层。练习。练习。练习。晚上演出前的练习。点击鼠标,把音乐从音箱里放出来。愿它是云。第五层。白蛇吐信,我用句子试探世界。这是奇妙的维系。身体跟着句子的呼吸摇动。你看,并不繁复的五层,还算听得过来的宇宙。只是,那离你太近的,终归于沉默。那过于响亮的,总无法持久。那被你遮盖的,才是宇宙的深处。我是MC,不甘心藏匿的天工巧匠。我洒出语词。它们密度不一,它们咬在一起,闪闪发亮,引人入胜,遮天盖地。为什么要说出来,唱出来?在自己录制的宇宙边缘,没什么理由不沉默。说出来的诗意,都太刻意。只有窗外,依旧风和日丽。
Mar.22.2013 AM 01:32 (街头闲聊的城市隔阂)
演出完,我们逃到门口,抽烟,透气,闲聊。人就是原子,在不同城市,不同的空间,散漫游动,见面闲聊。上海话,北京话,成都话。一个城市有自己的口音吗?这是一种障碍吗?口音是空间的通行证吗?朋友说,在北京,有贴心的朋友。在上海,大家都是朋友,其实根本说不上话。成都话?我他妈的就一个人。可怜兮兮的。很可怜的。我们在每个城市,寻找自己的躲避之处。我的朋友就躲在shelter。我说,山清水秀,心里苦闷。还有人还想去北京呆一年,不在意空气。在临街的门口,我们的对话就这样聚起来,我们就这样躲起来,又随着交通声散了,甚至都没有来得及酝酿一场雨。所有的闲聊偶遇,只不过是摇摇晃晃的临时建筑。它没什么重量,也谈不上危险。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的是絮叨。讲出来,让它飘走,排空自己。
Mar.22.2013 PM 04:51 (空旷公园的魔幻剧)
空旷。城市里珍稀的品质。空旷。张大嘴把时间的密度稀释下来。声音蹿在气泡里。有鸟高鸣,交通嗡嗡,脚步踢踏,交谈琐碎。我喜欢公园。空旷之地,都市丛林的应许之地。人们在公园散居,发梦。下午五点,朋友在公园等我。两个姑娘,围坐着聊天。我悄声走近她们,在丛林中听到一出魔幻剧。你简直就是铁皮驴。阿胶驴。是什么啊?还没想出来。你都抽起大麻了也想不出来。你真是。你要会翻跟头就好了。那可是技巧锦标赛。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恩,真好。
Mar.22.2013 PM 09:15 (没名字撞到名字)
精气神的哥们儿在酒吧准备演出。开门,黑胶的味道扑面而来。人和机器的对话。有温度,通过指尖,摩擦,反复。优雅的。贝斯低沉。鼓手干净。最早的黑胶是虫胶。让原料转起来。虫子,树木,胶的芬芳。摩擦,就是虫子吐出来的胶泥。没名字的你撞到名字。小老虎,这是你祖宗!
Mar.23.2013 AM 09:11 (呢喃清晨)
在上海的清晨醒来。男女呢喃,低声轻笑,私密有致,柔软的撕开了一天。对我来说,不是每个清晨都可以这样醒来,更谈不上私密。私密,不是来自语言信息的晦涩,也不是轻声细语。不,不是这回事儿。它直接来自身体内部的殿堂。鼻腔,腹腔,胸腔。它不急着表达什么,它简单呈现,共鸣。那又如何才能收纳这美好的清晨?我是一名农夫。在上海的某张床上,有我灌溉的私有之地。打开手机,录制,截取,我在清晨收割。能收割的,便不是那些看不见的,听不到的,或是遮盖的和微小的。所谓私隐,不能收割的它们,还盘踞在身体的殿堂里。我等着。
Mar.23.2013 AM 10:38 (澡堂丛林)
我被吓到了。在通往泳池前的更衣间。孩子和父亲,站在狭窄密集的热带雨林,水流刷刷的从屋顶降落,砸碎一地。犀利的沐浴喷头,孩子在水中喊爸爸,爸爸和孩子说话。空空荡荡,着不了地。我站在自己的雨林里。耳朵睁不开。眼睛也睁不开。我们被万物的声音包围。我们与万物相处,我们在万物的声音里,孤独对话。
Mar.23.2013 AM 11:46 (孩子直通天地)
差不多一个小时。孩子和父亲从泳池回到更衣间。沐浴,更衣。木质的长凳,铁质的存衣柜。我也在一旁,更衣,侧耳。父亲善命令。语言是清晰的指令,复杂的逻辑,成年累月修建的权威。出来。冷的。穿衣。快。出来出来。孩子只是欢乐的叫唤,发出愉快的寒战声。没有说不,也没有说嗯。不是反抗,也不是揶揄。孩子不善语言。孩子直通天地,枝繁叶茂。孩子住在自己的世界。没有争锋,无谓相对,也没有对话。孩子抓不住。
Mar.23.2013 PM 05:44 (口音的崇高与声音的转译)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不是上帝。我也不想思考。听人说,我们都在戏里。别的管不了,眼下这房间里,坐着个小丑,念着一篇悼文,有了出独幕剧。我在舞台上,也在舞台下。我在小丑身后身前,晃来晃去,听了又听。忽远忽近的,还有女朋友的高跟鞋。今天是无数个祭日中的一个。Curt Kobain。今天纪念柯本。死去的人纪念活着的人。I am sitting in the room。在这个房间里,声音被不断转译。Kobain的音乐,被转译成广播里带口音的长悼文,我把它们随机转译成喷嚏,拍手和大笑。我们都在戏里。我们相互观望。我们各自成为别人的鱼肉。逻辑。口音。语调。节奏。语词。还有杯子吗?有。房间破了。
Mar.24.2013 AM 11:52 (左转弯介入右转弯)
耳朵快震聋了。在公交站和女友等车。一辆大公交。转弯进站。右转弯,左转弯。喇叭放在窗外,持续重复指令。巨大的喘息轰鸣,遮掉了雨点落在候车棚顶的声音。听起来,我正面对一头怪兽。我录了下来。恩,但是为什么?被侵犯?用录音抵抗?抵抗什么?这巨大的,左转弯与右转弯的机械怪兽?这是一种景观?一种可以复制的景观?不是复制。也不是消解。聆听让物件敞开。让自己敞开。声音让人缓慢。你无法快速断了干系。这就是你介入世界的方式。录音没有尽头。不是截取一个片段,而是生成一个藕断丝连的新世界。声音,是世界持久的生命力。大公交,是混杂的生命体,机械嘶鸣和女声的导航。它是流动的。录音是生命时间的孔洞。经历,共时,在场,是最重要的意义。声音和生命本体,合鸣。
Mar.24.2013 PM 02:45 (街角水果店里电视机和我们对白)
午后,街角水果店的女售货员。店里一角的电视机。现场正在发生两段对白。电视里,是女子的倾诉。钢琴和小提琴,标准的催泪配置。对不起。男人的道歉。哭诉缠绵,简简单单谈恋爱。简简单单相爱。电视外,我们和女售货员简单交谈。零碎对话。波澜不惊。我们是过客。我们直呼物品的名字,讨论草莓,橙子,价钱和水果的成色,听塑料袋的摩擦,电子秤的滴滴。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我都会不停遇见街角饭馆和小铺里的电视机,服务员和售货员,以及散落的对白。什么是日常?在过去的半个多月,我打开了耳朵。但是什么让我按下手机上的录音键?听起来,没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只是这些重复的事儿,让我知道了日常的发生。它们碾过我的身体。我的录制,也成为这种日常的一部分。复制的目的,不是保存和回顾。我需要的只是行为本身。用一千个,几万个,无法分辨的日常,来复原日常消逝的肌体。用每一个醒来的细微当下,来触摸日常被淹没的宏大。真的是这样吗?
Mar.25.2013 AM 12:35 (凌晨的鼾声辗转反侧)
我听过不少的鼾声。只有真实的陪伴,才有机会听到鼾声。父母,亲人,朋友,爱人。床。房间。家。在最私密的空间,我听到鼾声,呼吸受阻,舌与软腭颤动,产生粗重的声音。再夹带些磨牙,梦话,辗转反侧。在凌晨午夜,我们毫无防护。鼾声,又称睡眠暂停综合症。沉静的夜晚,有人试图中断与世界的无声共振,勉强着发出声响,开始对话。我被唤醒,安静的聆听,手足无措。
Mar.25.2013 PM 07:57 (三轮车的高频精致入脑)
被击中了。细微闪亮的高频,拉得长长,透明而精致,直入脑皮层。我追了上去。载满啤酒瓶的三轮车,晃晃荡荡。金属,玻璃,液体,并不耀眼的早春阳光,奋力的骑行与垂垮的车体,贴身而过。这还是街头,可以有荡漾的诗意。你可以说,自从开始录音,我不再是战士。做个园丁如何?观测,揣摩,修剪,培育,鉴赏。我们总想留住点什么。每段被截取的声响,像极了这都市浪荡子复辟搞出来一大堆微缩盆景。可远观,亦可亵玩。
Mar.26.2013 AM 07:45 (闹钟是完美自我训诫的助手)
在清晨,我们如何醒来?难得不被唤醒。闹钟是忠实的狱卒,完美自我训诫的助手。它与身体对抗,以割断呼吸节奏,摧毁安静的方式,提醒秩序的存在,时间的流逝。奢侈的是自然醒,让身体与日月草木同辉共暗淡,自然的醒来,而非与城市或是他人同醒。起床的痛楚,是都市生活的最大伤疤。如何可能回望生活,自缓慢中寻找拥有过往的痕迹?我们想要记住某个清晨。可我们习惯的,是忘记所有具体而微的清晨。我们能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种类的清晨。比如今天,窗外警笛长鸣呼啸而过。
Mar.26.2013 PM 04:40 (时间就是一池子水)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时间就是一池子水,很多时候,没有风声,也觉察不到流动。我也喜欢呆坐着,站在池子中央,与万物相处,享用静止。当然,只要抬头,你也能看得见声音,时间流动的风向标。现在是下午四点四十分。隔壁在装修,电钻钻进墙里,风向标向北。我拖动身旁的空椅子。喝口水,又放下杯子。随后咀嚼几口薯片。又打开微波炉,关上,转动时间标尺。我什么都没有放进去。我把那一刻的时间放了进去。这刚过去的一分半钟,池面水波荡漾。与万物对话,让自我与此刻生活空间的物件,一同拥有边界,也划出相互的距离。
Mar.27.2013 PM 03:01 (燃烧植物置换空间)
还有最后一口要不要?好啊!可到底,是什么的最后一口?呼吸,幻觉,心情,现实?植物种在音乐里。这是听不见的音乐。没有聆听,只有漫游。不是时间的缓慢,而是空间的置换。我在音乐的巨大空间里。那些具体而微,可触摸,无穷无尽的物件,跟随目光所及,自我繁衍。在这样的空间里,花上些时间端详每一样物件,准确说,这是让人欣喜不已的度日如年。此刻,你听到这段录音,音乐在朋友家不大的客厅里,薄得像一层纸,一张贴在身后的墙纸。而我在另一个世界里,听不到你。
Mar.27.2013 PM 05:30 (谈什么旅行啊)
植物燃烧已尽。朋友们开始讨论旅行。朋友的女朋友,之前在泰国,现在又跑到印度去。她的微博,我给你看。挺棒的。又有朋友说,要四月底走。我在一旁呆坐。这是上海,我还在旅途中。过去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不同城市游荡。旅行,换掉点时间和空间,看到些自己或他人生命的新痕迹,以此憧憬些变化。有新鲜,也有不安。我没有离身去看朋友的微博。我选择追踪耳边松垮的爵士小号,闲散的钢琴。多简单啊,我们随时可以神游,双脚未动而离开自己熟悉的时空。过去三个星期,我打开耳朵聆听。对我来说,耳畔随时盛开新世界,和我脚下的现实相比,这不是旅行,而是实时的共生。
Mar.28.2013 AM 10:59 (头太方了进不去山洞)
城市里交通的噪声,就是挡不住的洪流。更准确点,是钢铁颗粒的洪流,常把我们脑部的河床冲刷得干干净净,麻木不堪。这玩意儿,容易让人疯癫。我身旁的女伴,站在洪流之中不肯挪步,只是绕着我打圈。她嘴里嘟囔着没有语义的哼唧,一点点靠近我,随即又喊我的名字。她把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削掉一些,替换一些,重新摆放起来。她突然靠得近近的,声音发的很大,得意的完成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只小老虎,他的头非常方。有一天,小老虎走到一个山洞边,他用它的胡子瞄了一瞄这个山洞,他怎么也进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头太方。
Mar.28.2013 PM 02:26 (易拉罐翻滚在街道)
街道川流不息。被各种声音包裹,挤压,冲撞。人们路过,穿过,滞留。没有人占领街道。有人沉默,有人发声。人们熟练的使用街道,舍弃街道。我痛恨街道的麻木和无趣。每次和女友外出,我都想制造些声响,找些乐子。街道需要游戏。踢,踢,持续的踢一个易拉罐。易拉罐在水泥的街道上,翻滚。踢,再踢。就像不经意的用石头打了一个水漂。踢,再踢,然后用人声轻快的模仿金属蹭过地面的声音。声音是权力,一种随时可生产的标识,一种可再生产的结构。街道需要游戏,但街道没有孩童。每一声,都在期待下一声。汽车到站了。翻滚的易拉罐停止。今天,女友对街道的占领结束了。
Mar.29.2013 PM 03:08 (随手打开录音随手打开身体)
对我来说,录音快要成为一种习惯。随手就来,未经思考。它不记录生活。它不是时间的留存和追赶者。更多时候,它是个预言者,一个旁观的神。它预支时间,帮助我想象生活的轨迹,那些未曾注目的凹凸起伏。这更像是冒险。在上海,和异地的女友共处。我敏感于时空的变动。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里,录音行为,隐约成为一种预判。这个下午,我随手打开录音。我们随手打开身体。这些亲密的关系,追随身体的轨迹。对话,根本上是身体的交流。声音是震动。它标记生命的痕迹。它让每个行为变得有迹可循。由此有话语和呢喃。言语的节奏,语调,质地,是身体的产物。震动身体,自然发出声响。今天我是按摩师。拍打身体。嗯..嗯..嗯.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嗯嗯嗯… 嗯嗯….嗯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拍打她的身体。身体给予回应。就这儿。就这儿?我使劲儿敲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儿吗?隔壁仍在装修,打孔枪拍打墙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Mar.29.2013 PM 07:04 (界面之声与机器说话)
和女朋友去看朋友。我们在房子外面,我们与远处的交通声伴随。房号,数字,按钮。我们在金属界面的另一边。叮当,叮当,叮当。持续,但没有回应。女友慌忙说,按错了。换一组数字。拿起话筒的声音,没有人说话。门打开了。长长的鸣叫,直到门关上。我们通过很多数字,机器的界面,与世界沟通。有ATM机器,也有门禁。通过机器的沟通。一系列的数字,去往另外一个空间。我们喜欢让界面有声音。如此,我们得以知道,界面与自我的痕迹。开启门禁。你是谁?上了电梯,出门,见到朋友。
Mar.29.2013 PM 09:26 (女人们的聊天垂吊在屋顶)
约会约会约会约会。这是女朋友的朋友们。在我的左边,右边,正面,侧面。女人谈论男人。谈论家长介绍的对象。男人要求发照片。女人不愿意。发照片就是扒光了自己。说话呢?不扒光自己吗?交换照片吧。不发的话,我们还能聊会儿。让我们谈论条件。男权的世界,女人们的聊天垂吊在屋顶,变成圆乎乎的迪斯科球,闪闪亮亮,晃晃悠悠。我在一旁,嗯了一声。在女人的世界里,我就是个男权的代表。我就是迪斯科球垂吊在屋顶的轴。一根黑色的铁轴。背景电视的音乐,持续响起好声音选秀里莫西子诗的音乐。他在唱,阿姐,怒。阿姐,怒。
Mar.30.2013 PM 01:53 (世界就是一锅喃喃碎语的残粥)
午后,起了点风。我们经过人们,人们经过我们。风经过我们,我们经过风。有人在扫地。时光流逝,不带来水的声音。耳蜗里有细致的触感,来自植物对大地的抚摸。鸟鸣,脚步声,街头对话与嘀咕,呼唤孩子的名字。 我站在街上,我的世界在灶上躺了十天。这一锅尚有温度的残粥,只剩下些喃喃碎语,语意模糊。
Mar.31.2013 AM 10:01 (胶带会说话但词语已经衰老)
打包打包打包打包打包打包打包。把东西放进纸箱。盖上箱子。麻利的用胶带绕过箱子。用手抹,贴紧。剪断。扔掉剪刀。再绕两圈。重复一千遍,一万年。胶带仍然会说话,但所有的词语,都在你学会的第一天,开始衰老,开始死亡。
Mar.31.2013 PM 08:20 (把世界切成薄片换取一秒钟时间的味道)
把世界切成极薄的片,放嘴里,还没闭嘴就融化。这就是不到一秒钟,时间的味道。
Apr.01.2013 PM 01:47 (溪水冲过后背)
你需要下一段时间,下一个生活,才能知道现在是什么。只有你踩在草丛,在丛林里潜伏,让蛙鸣炸掉头顶,溪水冲刷后背,飞机轰鸣的脉冲如远方浅浅的雷鸣,你才知道,我们现在不在城市,而在山里。
Apr.01.2013 PM 02:14 (把郊区录下来藏在兜里)
郊区有郊区的味道。在山里,世界的密度被稀释下来了,清清淡淡。因为空间被打开。对,就是四目所及的最大距离,所能定义的空间。鸟鸣蛙鸣,电视机里粤语飘过,马路上驶过的车辆,天空飞机长鸣的发动机。我录下这些声响,藏在兜里,把他们当成糖果,慰藉自己的过去。
Apr.02.2013 PM 07:24 (我们不说话的时候食物也没有说话)
在餐厅吃饭。我没有说话。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我们不需要说话。这个世界自己在说话。我们说了,这个世界也听不见。我们不关心这个世界是否听得见。我们围坐,用语言建立一座高塔,生成一朵蘑菇云。一桌上就餐的人,拥有同一场暴雨,以及一种同样的病痛。人们说,嘈杂。无序的时候,声音沦落为一个平面。我们不说话的时候,食物也没有说话。
Apr.02.2013 PM 10:36 (不知为何丢失的20分钟)
这是最后一段音乐。片尾,还有些静默闪烁的鸣谢字幕。放映厅里,就我一个人。我叹息,咳嗽掉了下来。没有急着起身。椅子嘎吱作响,情绪不断。我安坐了会儿,走出电影院。看完电影的情侣们边走边算,刚才电影的时间里,不知道为何丢失了20分钟。
Apr.03.2013 PM 08:38 (太说了)
操,这电影还真是挺躁的。我要去医院现在都好不了。啊?公交车里的液晶屏在播放儿童节目。这附近没什么电影院。3D啊!比你家干净多了。我,站在大卫和朋友旁边。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他在干吗呢。朋友以为我在看手机。我在录音,朋友以为我在拍照片吧。玩儿吧?玩儿呢。不后退就走路,怎么就不见蜻蜓的小宝宝呢。因为蜻蜓把小宝宝生在水里面。你这麻烦,可是麻烦总来找我。一年之后啊,蜻蜓才能长大。草,说会儿啊!现在我觉得自己太说了。卧槽,我感觉自己有点像个话,对吗?哎呦!哎呦!公交启动,我们都快被晃倒在地上。
Apr.04.2013 PM 03:51 (复古游戏机的潮汐)
潮汐澎湃。不断等分重复的音阶。我们卡在八比特的模拟游戏机里。老四,老四,那跳舞没了。谁是老四?老四在和他老婆说话,十五块的桶,一个就够了。老四,老四。潮汐澎湃澎湃。不断等分等分重复的音阶。我们卡在八比特的模拟游戏机里。老四,老四,老四,那跳舞没了。谁是老四?老四在和他老婆说话,十五块的桶,只要一个就够了。老四,老四,老四,老四。潮汐澎湃澎湃澎湃。不断等分等分等分重复的音阶。我们卡在八比特的模拟游戏机里。老四,老四,老四,老四,那跳舞没了。谁是老四?老四在和他老婆说话,十五块的桶,真的只要一个就够了。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
Apr.04.2013 PM 12:15 (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
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一家数口,吃饭聊天。家常岁月,都在嘴里咀嚼。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同事是嚷嚷的外地人,不懂客气话,撞人赔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因他人之祸,自己得到些福分。换岗之后工作要轻松些。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父辈们的生活里,人情世故,机缘巧合。我觉得陌生得很。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吃饭就是吃饭。吃饭不是吃饭。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每一个桌子,每一个家庭,每一顿餐食。每天餐桌上发生的,也在餐桌外发生。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我们就是这被吃掉的食物。
Apr.04.2013 AM 11:35 (叹息里窜进来两个电话)
24小时不知疲倦的生物,日常家庭生活戏剧的舞台设定者,剧场外醒目的霓虹灯。还是那台电视,点亮了奶奶家的客厅。我也在,沉默的看电视,看生活不停息的上演。奶奶一直在和家人唠嗑,生生死死的事儿。最后一声叹息和几秒停顿,把铺开的谈话和倾诉,不着痕迹的抹掉。我在一边听着,嗑瓜子,没说话。奶奶又接了个电话,说,赶紧来吃饭吧,什么都别买了。买豆汁儿了?丽华买了豆芽韭菜,正在厨房炒,也叫了菜了。都是些豆制品。我溜到厨房,妈妈在切菜,我还是没有说话。奶奶说,把桌子搬来,吃饭吧。桌子摩擦着地面,一路尖叫。
Apr.05.2013 PM 03:24 (悉索咕)
悉悉,索索。悉。咕,咕,咕,咕,咕。悉悉,索索。悉。咕,咕,咕,咕,咕。
Apr.06 2013 PM 01:35 (凉的热的凉的热的)
在朋友家,三个大男人挤在厨房做饭。我给朋友打下手。灶台就在身边。尖锐的燃烧和喷发,轰鸣的噪声,锅碗瓢盆的磕碰。厨房的声量,总是生活活力的最佳指标。我们在赶时间,等其他人买来佐料。厨房里有很多的决定要展开。这些决定,要越过厨房空间通往其他的空间。因此,在厨房里传话,是一门技艺。你得简洁。这次是有关凉热的选择。凉的或者热的。朋友把最合适有力量的词语捡出来,狠狠甩出去,让下一个人接住,裹上些情绪,再甩出去,传递下去。其他剩下的,抱怨嘀咕或是絮叨,就留给自己,让它们和持续喷发的灶台和抽油烟机一起,燃烧一会儿。催促或者等待,生活的节奏在铁制的锅铲里,在翻腾的饭菜里,死去活来。
Apr.06 2013 PM 06:06 (看车看车千万别动)
我,和女朋友,还有朋友们,在胡同里踢毽子。朋友带着墨镜,把毽子踢得远远的,给对方出个难题,嬉闹嘲讽,锻炼身体。胡同是公共空间,踢毽子是群体活动。有陌生的阿姨骑着三轮车过来,远远的吆喝,千万别动,千万别动。在这胡同空间,我们是一群流动的鱼。阿姨是一头鲸鱼。女朋友说,瞄准吧。阿姨回答,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2022.03.13
2013 ”日常生活炼金术“计划 – “寄生/声” 作品设定笔记
《日常生活炼金术》计划:【寄生/声 SPY VOICE】项目方案
这是一个长时间持续的计划。这个项目,需要从一种理性的审美和批判冲动,转换为日常生活世界的诗性。
1)形式:
• zafka找到Jfever配对,两人进行。
• 两人通过智能手机app(SPY VOICE),每天进行快捷录音每天录制2-5个片段,并即时上传到tumblr发布。
• 当天相互聆听对方的录音,进行即兴的声响写作,并即时上传到tumblr。
• Tumblr分为两个,分别为 spyvoiceleft & spyvoiceright 。意为左右声道。
2)时间:
• 第一阶段:一个月30天,每天频密在两人之间进行。也不一定一个月,看到时候的进展。可以到一个点上终止。但需要有一定的量。
• 第二阶段:30天。再加工与再呈现。
3)双方各自思考的关键问题
• 参与者如何藉由聆听,录音的实践,去理解自己的生活,周遭世界以及自我?想象最后所有的声音素材呈现在一起,是一个怎样的场景?你想如何去录音,去呈现你的生活?要想象30天后,所有声响呈现在一起,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 参与者如何通过聆听他者声响,藉由对于他者和世界的声响想象,并通过声响写作实践,深入探索时间和声响的关系,并剥离和重建附着在声响上的社会和文化意涵,融合现实与虚构,由此绘制一副基于声响的,自我和世界的图谱。
• 参与者如何藉由阅读他者的文字,来获得回馈,并由此修正和寻找到自己的方式,通过聆听和录音建立自我的日常生活世界。
• 声音部分,文字部分,应该相互独立。各自有自己的美学系统。
4)项目进行中的原则:
• 坚持。不缺席。
• 专注。通过声音和写作本身进行。项目期间双方对各自内容不交流(项目本身管理事宜除外)。
• 身体。关注身体的敏锐。不管是在录音还是在写作中。
5)录音的规则
• 聆听:对自我,生活与世界的一种审视。
• 方式:即兴的,即时的。
• 数量:每天2-5段落。(一个月,以每天1分钟的片段计算,总量在至少30分钟。)
• 长度:每段录音,录制时可以随意长度。但长传时会被压缩并自动截取为最多两分钟。(每一种科技都天然的有一种限制性)
• 内容:不能全是对话,对话,对话。是对自我日常生活的全部理解。要尝试建立自己的方式通过录音去记录和表达。
• 发布:即时的。只要网路允许,即时发布。如果不能,当天的一定当天发布。
• 发布:除了网路发布,请定期从手机中导出所有原有录音材料,原大小和长度。备份。很重要。
6)阅读的规则
• 每天阅读对方的写作,并由此启发自己的录音。录什么,如何录等等。
7)写作的规则:通过写作重建声响
• 内容:不是通过写作去简单描述你所听到的。要关于声音,关于自我,关于周遭世界。是解构,思考,和重建。
• 方式:戴耳机。听的时候跟随即兴写作。重复听。
• 体例:用第一人称写。混合真实和虚拟。
• 体例:标题,就是录制的声音自动生成的时间标题。
• 数量:不用对应每天的录音每段都写。但至少应该有2段。(至少60段。字数在1万字以上。)
8)第一阶段的呈现:Tumblr网页在线
• 一个tumblr网页/网址,就是某段时期(一个月),关于某个人的生活简史,关于某个人真实与虚假混合的自述史。一段由真实声响,碎片化记录的生活,一段由他人的寄生/声,所生产的生活。
• 视觉上:大量的方块。黑白。接近一本书,一个卷宗。
• 核心线索:时间点。打过生活的一个一个的时间点。层次不齐,可以不停的下拉,接近于时间之流。
9)第二阶段呈现:文字与声音装置
10)第三阶段呈现:声响剧场表演
2022.03.13
2013 “日常生活炼金术”计划 – 声响想象,声响写作与自我重拾
2005年到2008年,我一直在进行实地录音,使用各种大小录音设备,去监控,记录,理解,介入我所面对的日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强调主动的聆听,强调基于政治和社会学的逻辑,去理解城市声响背后的权力结构,唤醒耳朵,就此实践主体性的解放和反思。而后,我又进一步尝试超脱宏观逻辑,以个人的城市声响微观地理学为面向,通过个人声响游击战的方式,以脚步加头脑和麦克风度量城市,让日常聆听更易接入主体的解放。最后,我又进一步把声响看成剧场,认为录音和聆听者的角色和行为,可以更为激进和即兴的成为现实剧场的一部分。
2009年至今,我基本不再随身带着录音设备,随时实地录音了。因为我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多大程度上,聆听和录音的介入实践,可以成为个体持续的日常再造的有效机制? 我想重新找到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能深入日常生活的时间,能重建,能缓冲,而不是简单的消逝。在2011年【0526】http://20110526.tumblr.com 项目当中,我做了初步的尝试。我一会代替胡昉描述录音的情景,一会又作为聆听者揣摩那个与我不相干的时空,一会我又直接代替胡昉来嘲笑聆听者这个角色。 以前我是隔着一个麦克风去聆听这个世界的,但揭开这个工具或媒介的帐幕之后,为什么艺术家非要去做实地录音呢?
我同意台湾声音艺术家林其蔚在《超越声音艺术》一书中所言,【今天的声音创作…应该被当成艺术家与聆听者共同参与的交换过程,声音-空间本身变成了一个观众可以使用且自行定义的界面,提出声音的物性,既是将现实听觉环境变成文本,也是将文本爆破为现实,聆听的对象既是我们的环境与世界,也是我们自己。】
2013年开始,我启动《日常生活炼金术:声响想象,声响写作与自我重拾》计划。该计划围绕声音,文字,身体,表演等多个维度,探索日常录音,声响写作,文本诵读,剧场表演等多个形式的融合。在传统的聆听和录音实践之外,发展新的日常声响实践个体新技能,重建日常生活世界的诗性,以及声响,时间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1)声响想象 (Sound Imagination) :
• 想象和重建世界的新能力:一种透过听觉重新认知和反思自我,重建世界的能力。
• 探索和提问世界的新方式:听觉想象可以深入到什么程度?具有多大的能量?以声响为轴,重新想象和建设世界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旅程。它接近于一种神秘之术。它需要想象力,需要一些艰苦的练习。对日常声响的记录,我们需要投入时间,专注,以身体和情感的体验,再次穿越时间之河流,以聆听为轴。这种想象,存留于记忆,情感,被日常遗漏。它需要被激活,成为习惯,成为仪式。
2) 声响写作 (Sound Writing) :
• 即兴的写作:听觉的身体性,顺应/归顺声响的写作。我强调写作的即兴。戴上耳机,把自己扔进声音里,依靠身体和直觉,写作。通过这个过程,通过对他人生活的监听,扮演,写作重建,历史重写,来获得自己的解放。之间,要处理自己,声响,与写作所使用的第一人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文字是客观之物。即兴的写作,呈现了世界暗自赋予我们的结构。
• 声响的重建:我强调写作的重要性。去聆听,同时去描述,去重建声响。为何要书写?书写本身是极具画面感和仪式感的一种实践。找到自己的方式,进行声音的书写。发展一套语言,重建自己所面对的声响世界。可以基于传统的文字叙事,也可借鉴声音诗sound poetry技法和传统,探索更多做法。
• 时间的重建:建立对时间的理解。这里要强调的,是聆听理解声响,抛却杂念,通过写作去理解声响,居住于声响之内,找到自己的方法,在时间中重建时间,获得一个微观完整的时间。通过是书写声音,来释放自己。
• 自我的关照:重建对世界的想象和认知,通过声音,转化为“客观的”文字,去想象他者的生活,同时阅读他人依据声音写作的自己的生活,得以反思和关照自我。
3)声响诵读与声响剧场(Sound Performance & Sound Theatre)
• 阅读他人的声响写作文字,可以参看自己,获得一种重构自己的机会,同样是一种反思,是对自我世界的一种颠覆,反观,或是补充。
• 诵读,让文字通过话语,通过声音本身,重新获得体验,打破这种结构。诵读,让他者的文字重新通过主体的声音,让客观化的世界重新主观化,通过语言重新进入身体。让之间的差异性,成为重点。让各种拗口,失误,不习惯,奇怪,也让各种自然,顺势,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 现场即剧场。剧场即现场。通过表演重新获知。
4)自我重拾与寄生 (Self-Revisioning & Parasitising)
• 通过整个过程,录音者,通过录音,阅读,诵读,获得自我的参照。写作者,通过聆听,写作,再聆听,也获得自己的参照。
• 寄生:通过寄生,获得日常的意义。
• 个体:通过揣摩,想象,练习,去获得个体的完整性。
• 复制:如果让这个过程,成为别人可以重复寄生的过程。
2022.04.04
2008 ”平行世界专栏“ – 城市中国
专栏1:重构的城市与电子自我 文/ Zafka
从今天开始,跟我一起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需要舟车劳顿——静止的电脑屏幕,从来就是互联网时代现实衔接虚拟的窗口。窗外,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正悄然向你打开——在3D虚拟世界,你可以是癫狂的政治家,自由迁徙的公民,毛孔里渗血的商人,天才的科技怪客,昼伏夜出的舞客,抑或任何你想要的self。你可以操控你的化身,在线建设这个世界的土木和规则,然后交易,社交,娱乐,定居抑或游历。
十五年前Neal Stephenson天马行空的笔端,“Metaverse”(虚拟实境)是这个尚未曾出现世界的别称。现在,从硅谷到北京,科技支撑的3D虚拟世界部落,已经开始全球游牧,划定未来平行世界的新版图。这是一场看得到的革命,在这个全球性的社会新空间,你可以不参与,但你必然不会错过。
对于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William J. Mitchell曾有个非常曼妙的比喻──“在我们布满沟壑的大脑上生长出来的更新的神经结构”。我们已经见证了互联网如何以代码重建时空,以看不见的cyberspace,深刻改变关于城市,关于自我的传统命题。如今,这个松散平面的神经结构已经长成了全新的“世界”,将我们已经被互联网和电子时代逐步解构的传统城市和自我,彻底放逐到全新的3D虚拟空间。这不断自我繁殖中的虚拟世界,正在复制和超越现实世界的逻辑,跟现实世界竞争,同时加速融合。
传统的城市和自我,是关于疆界的命题。我们一直在社区/城市/民族国家等疆界的单元中生存。互联网和电子的时代造就了电子游牧,脱离传统城市的开始。政治界限和真实公共空间的有效性,公民权,公共场所和城市景观等概念,已经在无边界的信息流冲蚀下垮掉。这个过程,是从水井到城市管道,再到比特管道的过程,是后定居的游牧时代,都市和自我重构的过程。
现在,一切似乎要从头开始。重塑的虚拟身体重新生存在重塑的虚拟空间。越来越多人已经卷入,新的高度可视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已经形成。沙龙、咖啡馆等传统公共领域的最重要象征物在虚拟空间被重建,人们再次围绕壁炉,坐而论道。朋友、亲人、团体,重新回到了可见的虚拟空间,安静的坐下来交谈。虽然这些仍旧发生在虚拟世界,但3D化身和空间的存在,恢复了“在场”——这一人类交往中最重要的感受,适度回归了传统真实交往的心理和结果。
重建的虚拟社区/城市/国家,是成本最小的世界,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实验成本最小的平台。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定居,再迁徙。从今天开始,选择狂野新大陆——奠基于加州的Second Life,或者发轫于北京的HiPiHi,开始你的新生活。HiPiHi相信,这是古老文明的矩阵革命。东方HiPiHi的虚拟世界里,人们开始重新聚集形成社区。我很想成为HiPiHi大陆腹地的“花溪深处”社区的村民。这个强调“隔离之美”的古村落,小河流水,饮酒当歌,已经是今日的常事。
虚拟世界,CODE仍然是一切的基础。华丽的砖墙,随风而动的草木,自由天外的人,都是代码操控的结果。但代码身后仍然是人。我要开始生活在这个平行世界,观察和记录这个世界的成长。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在一场彻底电子游牧的旅途中,寻找最后的家园。
专栏2:逃往虚拟世界 文 / Zafka(张安定)
在西方传统中,出埃及是有关救赎的历史。现在,Castronova说,人们正在第二次出走,重写历史。这次是从现实中出走,逃往虚拟世界。《Exodus To the Virtual Worlds──how online fun is changing reality》。这是一个资深游戏玩家,网游虚拟经济的全球头号研究先锋,印第安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Castronova在08年的新作。
过去几年,全球越来越多人投入越来越多时间在网络游戏,从现实中出走进入虚拟世界,形成了规模日趋庞大的虚拟社会和虚拟经济。Castronova预言,未来20-40年,积累的蝴蝶效应将改变我们的社会气候和现实生活。由于游戏虚拟世界的设计涵盖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等一系列规则,与真实世界的公共政策设计一样涉及评估人们的共同利益,并以此安排治理的最佳过程,两者被视为基本相似的活动。因此,与逃往虚拟世界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相伴,公共政策制定可以从虚拟世界中学习经验,提高人类在现实社会的幸福感。
理解以上推断的关键在于理解fun。人们花时间游戏是因为fun。有趣,一种感知和情感,一直是人类幸福感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游戏产业过去三十多年发展中关注的核心命题。游戏虚拟世界设计师们制定规则,创造社会秩序,维持一个虚拟社会和经济体的持续运转,目的是让参与这个世界的人尽可能获得fun,找到现实世界所不能给与的满足感,提升个人幸福感。但在Castronova看来,现存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设计,过度关注效用(utility),并没有足够认知和理解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性。当人们在虚拟世界获得足够实践经验,他们会要求现实社会的公共政策做出改变。
非常令人奇怪的是,Castronova没有提到目前所有的游戏虚拟世界都是追逐商业利益的产物。这样的追逐,虽然核心在围绕人们获得fun,但因为人性的复杂,fun体验的复杂,可能呈现的并不是理想国。
Castronova异常信任游戏虚拟世界的设计师,同样也沉迷他在魔兽等世界中的正面体验。一定程度上,魔兽世界还有其他西方经典的网络游戏,支撑游戏设计师和玩家的是其社会本身的理念沉淀。自由,平等,开放,每个玩家投入时间自由竞争,选定多元的职业,提升级别技能,参与社区,获取认同。而源自西方的网络游戏在东方演变为所谓韩国“泡菜”模式──打怪,升级,PK,不停的重复再重复。与级别和装备相关的权力争夺才是最让玩家着迷的地方,也恰恰是东方现实社会的写照。玩家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在游戏世界通过时间和金钱投入比拼来完成。这样的虚拟世界,只是现实世界无助的投影,距离Castronova所言引导现实社会公共政策的实践,基本背道而驰。
出逃虚拟世界,更多人参与体验和实践,不是逃往不能自定规则,数量有限的商业游戏虚拟世界。即使在游戏界,人们对fun的体验,现在要求更为开放和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更为真实的模拟现实社会。这样的世界不可能是由少数游戏设计师作为上帝主导的世界。这也是Second Life这样开放结构的虚拟世界当下流行的原因。在这样的世界,有关fun的定义与游戏并不是一回事。
更为开放的虚拟世界平台,因为赋予了玩家从内容到规则生产的最大自主权,已经成为当下最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实践和创新场所,引发了全球关注。虚拟与真实正在走向融合,相互教育和引导。目前在SL,有居民自主组建的共和国,还有经济和金融的创新实践。虚拟世界的实践已经跟真实世界挂钩,公共政策不仅学习虚拟世界经验,而且开始管制虚拟世界。
Castronova设想的未来,仍旧奠基在科技进步的技术之上。只有更多人自主的虚拟世界实践,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共识,才有改变现实的正面意义。08年以来,开源虚拟世界技术进展迅速。未来3-5年,每个人都可以逃往自己架设的虚拟世界,每个人都是设计师,都可以自定规则,同时也拥有更多的出逃选择。
面对同样的问题,相比Castronova,Cory,去年末刚辞职的Second Life的CTO, 具有更为广阔和深度的视野。虽然Cory笔下的《Collapsing Geography》只是一篇长文,但有关3D虚拟世界如何最终完成互联网重构时空的使命,拓展人类自由实践创新的空间,要比Castronova围绕fun的预测,更具分量。
专栏3:虚拟实践:两个RMB城市的意义 Virtual Practice: The Meaning of Two RMB Cities 文/Zafka (张安定)
两个RMB城市
4月初的某个周末,参加完纽约全球虚拟世界大会后,我去了曼哈顿切尔西区的Lombard-Fried画廊看曹斐的个展。她在3D虚拟世界Second Life中的RMB City——人民城寨计划,已经成为国际前卫艺术界和NY Times等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点。真实的前卫画廊,也同时成为虚拟RMB城市的纽约售楼处。世界各地知名艺术机构和画廊已经表现了极高的兴趣。他们需要支付不菲的价格用来支付建筑费用等相关费用,获取入驻混合中国高速发展城市多重符号的RMB City。进驻者会拥有建成后相应空间的两年使用权,也会收到两年后曹斐提供的空间相关记录和作品。
展厅里的白色模型让我想起了中国3D虚拟世界HiPiHi中的原点镇。我从纽约回来后不久,4月15日,原点镇迎来了首批107位申请入住居民。除此之外,现在这个镇还只有一面红旗,一个工地。也就是说,从资深居民上星空在论坛贴出倡议书,到居民集体投票成立8人筹委会,再到筹委会在HiPiHi支持下从各地进京(包括日本)召开筹备会议,制定规则,招募居民,原点镇的一土一木,还有社会和经济制度,都会由这群中国虚拟世界的早期居民自主完成。
两个城市有些神似。都发生在目前为数不多的可以自主创建内容和制度,极度开放型的3D虚拟世界。只不过一个是艺术家单枪匹马的实践,另一个是中国本土民众的实践。问题是,这样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场游戏?或是茶余饭后有关虚拟与真实的再一次哲学争论?
虚拟实践的历史
在过去几十年,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发展时,已经有很多哲学界和人文学科的人开始研究可能的冲击。可能个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主体性认同等地位。计算机仿真模拟了物理世界,数学世界,还有虚拟现实的计算机世界。这样的虚拟现实通过高度沉浸的头盔,身体数据服装,手套等成套物理的设备与计算机相连。但这样的虚拟实践,集中在人个体认知层面,挑战的是笛卡尔的身体与主体的两分。在全沉浸的环境中,主体对身体直觉完全依赖。
针对此种技术突破,提出的问题是有关虚拟实在和现实实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等。许多对虚拟现实可能带来的冲击的否定,都不承认其本身的现实性。认为虚拟实在技术只是改变了用户交换信息和刺激的方式,但是,感知并不只是交换信息,而且是一个识别的过程。识别依赖于作为背景的目标和信念。而其感知、目标、欲望的套装运作机制是漫长的自然选择烙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的,是现实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个讨论方向,指向了虚拟现实和虚拟世界的重大区别。虚拟世界的侧重点在“世界”。虚拟现实强调交互与沉浸,但通常是个体和极少数个体之间,个体与机器之间的交互与沉浸。
只有主体可以以大规模的形态同时交互,且可以自行生产和决定虚拟空间物体和活动时,才能形成真正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指向此在与围绕此在事物之间关系的富于意义的总体性。也就是说,虚拟世界不再是一个主体性相对立的客体,而是此在的一个结构方面。
这是集中在个体体验的层面的虚拟现实实践,并小部分的出现在军队,医院等科学研究实践中。相关的想像已经通过科幻小说传遍。Castronova在05年成名作《Synthetic Worlds——the business and culture of online games》中提到,在虚拟现实技术之外,一个“practical virtual reality”的实践,有自己独立的主线,多人在线网络游戏。
网游的虚拟世界开始走向群体的共同呈现,通过游戏设计者对世界的社会经济体系的设计,玩家通过角色扮演进入世界,开始互动并生活。Castronova的Synthetic world中说,通过身体的,情感的,还有货币的联系,虚拟已经跟真实没有办法区分了。甚至,人们已经出逃虚拟世界。这是一种高度沉浸的环境,世界存在于电脑的另一端。这种在虚拟世界的实践,已经开始出现了社会性经验特征,已经在投射现实世界的同时,开始改变主体的认知。
翟振明在《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中提到,只有完全沉浸的虚拟现实,才能塑造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始空间建造和空间性自身,非隐喻意义上的赛博文化和社区才有可能出现。目前网络游戏中,主题和客观化的替身之间,还偶临时约定无法填充的本体性断裂。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鸿沟。
从80年代末Active world这样的可以创造的虚拟世界,一直到Second life,这是一种对传统本体论情景的颠覆。约斯@德@穆尔说,“传统本体论把人类设想为一块石头,而在信息技术时代,硅元素设定了人类的特性。”也就是说,随着Second Life这样的虚拟世界的发展,3D互联网的发展,虚拟世界会通过链接社交,商业,娱乐,教育等,最终成为虚实交错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多方位的运用,高度自主的创新,是对真实世界的超越和复制。也就是说,在这个虚拟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实践,是可能成为原型来指导现实社会生活。
一句话,从虚拟现实的个体完全沉浸的梦想里,个体的虚拟实践,现在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RMB城市提出的问题
以上梳理,为我们讨论两个RMB城市的实践可能具有的意义打开了通道。麦克卢汉早在60年代末曾说,当今的艺术家应该好好想想,“是否有时间创造一个空间以面对他将面对的空间。”现在,Second Life这样的开放性虚拟世界,给艺术家以机会进行全新的社会实践,提供了艺术家机会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个人对曹斐RMB City计划的喜欢,不是从符号象征意义而言。已经有太多以中国符号来表达的绘画,雕塑和影像等当代艺术作品。这个作品从无开始,整个完成过程直接跟真实世界的艺术机构和制度,无论是在资本层面,还是在收藏体制层面开始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作品的迷人之处,在于一开始的虚拟实践。按照曹斐在城市宣言里面的表达,RMB是一个镜城,同时也是一个虚实不分的城市,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虚拟和现实的互为别处。
但最后,要最后跨越真实和虚拟的界限,最紧要的,是制度和规则的实践。建成后的城市,如果能迎来大量的人群在里面游荡生活,有关中国的符号,将在在一个虚拟空间,让那些习以为常的心灵,真实世界的作品观看者,再次重新经历和认知那些沉淀的主体记忆。虚拟现实概念了我们和信息的关系。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实践。也就是说,如果不仅是建城,而是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RMB City项目,最珍贵的将会是曹斐两年后提供的相关记录和作品。
同样在原点镇,早期参与居民,有着跟网游全体部分不同的特质,除了同样在一个新的世界找到一种可能,去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表达自己的梦想,这种实践,将更紧密的跟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专栏4:重塑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虚拟世界的爱心表达 文/张安定(Zafka)
从5月12日开始,四川汶川的地震令举国悲恸。通过这样一次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的大规模集体动员,学者季卫东在《财经》杂志的评论中写到,在废墟上隐约可见的“复兴共同体”,具有了最广泛的共识基础。而这个过程涉及到的媒体,涵盖电视报纸,2D互联网,还有3D虚拟世界。人们通过日益多样的媒体了解信息,同时又通过媒体表达和交换对于公共话题的意见。
在上一期的专栏里,我恰好谈到了基于虚拟世界的全新虚拟实践的重要性。而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如何应用虚拟世界这种新媒体,在虚拟的空间里,透过三维的虚拟化身和现实发生最大的联系。
2D网络与想象的共同体
网络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信息产生和传递的去中心化。地震的消息,最早是用户通过Twitter发布,之后才见于网络媒体和电视。Twitter作为个人的微型博客,是一种可以随时记录和发布消息,并与人沟通的工具。而地震中第一条被广为传播的有关地震的视频,是位于震中的大学生手机拍摄并上传的。几天之后,大量的来自地震区域的用户拍摄的视频已是数以千计。而全球各地的网民通过Blog撰写的现场报道,评论,在BBS中进行的讨论等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顺着信息产生的通道再往前一步,信息通过网络上不同的社区,通过每个人不同的social graph(社会地图)传递,讨论,再生产。电视虽然保持24小时直播,但却无法为散布各地的人们提供互动和沟通的渠道。用户产生内容的web2.0时代,公共性事件的发生,驱动了民意的集中表达和沟通。
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是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在同一个时间纬度的共存,最早是通过报纸为起源的传统媒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领域来达成的。哈贝马斯眼里的传统媒体,既是促进公共领域兴盛的原因,同时也因为基于商业和政治的垄断集权式传播而毁坏了公共领域。而网络的兴起已经证明,去中心化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改变,促使人们用新的方式打破时空,重新进入一个虚拟的公共领域。
但在学术界多年的争议中,不少学者认为,过于流动和匿名的网络文字交流,信息的多元和碎片化,加上完整意义上的空间感和共同存在感的缺失,使得基于2D互联网的虚拟公共领域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的缺陷。
虚拟世界的公民哀悼日
这次地震,在2D网络之外,包括网游在内的3D虚拟世界的动向,开始提示人们关于公共领域的一些新气象。作为人们在传统媒体和2D互联网之外的新型沟通渠道,这样的虚拟空间,随着网游人口和虚拟世界的增长,已经表现了比平面化的2D网络更为深度的内容。
举国哀悼日三天,魔兽世界等网游停止运营。在更多的网游和虚拟世界,有关赈灾捐献等消息,已经通过系统的公告等,传达给了网游社区的众多用户。用户不仅在虚拟世界里相互交谈沟通,表达爱心;开始通过公会这一网游的社区形式来组织募捐,发表意见,交流情感。不过,受限制于这些虚拟世界提供给用户表达工具和空间的有限,用户表达的方式仍然局限在语言等基本交流。
在全球最大的3D虚拟世界Second Life,其中的中国居民社区组织起来,募捐了相当于接近4000人民币的林登币。同时在HiPiHi,发生了中国本土虚拟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的居民自发社会公益性慈善活动。而整个过程突出特点,是居民自发通过创造对集体记忆的重塑,对公共话题不同形式的再生产。
举国哀悼的三天,HiPiHi和居民一起组织了大爱祈福的活动。居民和HiPiHi平台的运营者一起,制作了统一的服装,用于悼念的白花,蜡烛。原点镇,HiPiHi世界的第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由他们的建筑师设计了广场和纪念碑。第一天默哀,第二天献花,第三天烛光祈福。第三天的时候,虚拟世界调整了自然时间,世界陷入黑暗,并下起了雨。之前,居民已经选择自发号召社区同伴去捐款和献血。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贴出了鲜血光荣的海报,自己制作了鲜血证。这一切都是虚拟的,但这种自我认同和身份标示的新手段,却和真实社会发生着最大的联系。
重塑虚拟公共领域
这些发生在虚拟世界的公众性活动,并不是没有先例。在全球领先的3D虚拟世界Second Life的历史上,同样出现过居民自发追悼美国飓风遇难者,以及相关的募捐慈善活动。另外,国际防治艾滋病组织等公益性组织,同样在虚拟世界内进行过公众教育和募捐等系列活动。
在我看来,也许3D虚拟世界相比传统的2D互联网,能提供一个某种意义上回归古典的公共领域。不同于2D互联网网络,3D虚拟世界给人们提供了共同存在的可见的空间。人们通过虚拟形象聚集在同一个完整的虚拟空间里。在这样的空间,不是语言,而是服装,外表,举止行为成为了首要的焦点。
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更为敏感和多方面的,确认自己网络空间虚拟主体性存在的真实性。2D网络文字为主的交流中部分丧失的主体性,在3D世界得到了重生。不仅如此,仪式得以复制在虚拟世界空间。在默哀的现场,居民们在广场排队,一个接一个的敬礼,献花。所有的仪式,再次重复和强化了真实世界。
而虚拟世界因为更为创造性的表达工具和空间,提供了书写之外的更为复杂的形成和表达公共意见途径。现实社会的普通居民,在虚拟世界,利用在线的3D创造工具,可以更为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社区的同伴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塑造和表达集体记忆。不是语言,而是纪念碑和虚拟的身体,让人们在虚拟空间加速了复兴的共同体。
正如同我在上一期的专栏中写到的,基于互联网应用的虚拟世界平台,是一个更为社会化的平台,从而也具有了重塑虚拟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专栏5:经验世界的再延伸:作为教育新平台的3D虚拟世界 文 / 张安定(Zafka Zhang)
过去几期专栏,我主要分析了一些Second Life和HiPiHi的前沿个案,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角度谈到了以用户自由创造为核心的3D在线虚拟世界,可能怎样影响我们现有的真实社会。
事实上,在普通居民娱乐社交应用之外,现在3D在线虚拟世界已经初步展现出了机构用户应用的巨大潜力。尤其受到全球关注的是教育领域。现在以各种形式进入SL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多达400多所,教育邮件列表人数超过5000。 拥有超过225所知名大学和研究所加盟的国际非盈利机构NMC,在SL拥有超过100个大学岛屿。
就在写这期专栏前,我应国内web2.0教育专家和积极推动者,北师大教育技术学院的庄秀丽教授邀请,和学生分享讨论了3D虚拟世界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界的虚拟热度,非常真实。
传统教育,E-learning与3D虚拟世界
传统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知识的生产,存储,分享和流转主要通过学校系统。所谓书本化的知识和有围墙的大学。考虑到教育主要包括知识/技能传授与社会化两大任务,传统的教育体制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知识的垄断,以及对基于最优秀师资形成的学生社会化环境的垄断。
而互联网恰恰是去中心化的架构。通过降低时间和空间对个人存在的束缚,互联网促进的越来越扁平化的世界,拓宽了每个人自我提升的机会,扩展了人的经验世界。对教育来说,这是知识资源的去中心化,个人社会化方式的去中心化。知识的性质,生产以及流转渠道,都发生了变化。通过IM,BBS和SNS,全球各地的人突破亲缘,地缘等传统社会化渠道的限制,价值和伦理观念在全球交换。
Web1.0时代的互联网,首先使得电子化的知识可以通过网络存储和加速流转。帮助人们更有效率的接触到人类的知识积累。远程教育等也开始出现。Web2.0时代带来了E-learning的重要变化,也就是所谓社会化学习(social learning)。可读写的社会化网络,使得全球的脑力资源一同参与改写人类知识分享和积累的方法,也促进了教育和学习的改进。
在具有web2.0特征的,可在线读写,可分享的3D虚拟世界出现之前,基于60年代以来发展的虚拟现实技术,科研和军事部门已经率先用来实现专业知识的认知和过程模拟。同时,在国外的一些高校,也开始尝试利用游戏来学习。比如利用Sim City这样的游戏来模拟城市规划建设。
三种教育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通过人的真实聚集,传统教育的参与感,归属感等都具有明显优势。而社会化学习极度依靠个人的自我激励。学习者的参与感和归属感比较低。传统的3D虚拟环境,学生沉浸感强,学习有乐趣。但同时最大的问题是需要针对教育的需要由商业公司和专业人士提供内容,选择性和创造性低, 成本高。
经验新空间:Second Life的教育实践
目前SL上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全球教育者社区,拥有自己的email list,还同时频繁召开线上和线下的会议,探索虚拟世界的各种教育应用。
现有探索涵盖的方面非常广泛。虚拟校园与课堂,数据模拟,历史场景的模拟再造,艺术的创造性表达,召开会议和讨论,人工智能,游戏设计,产品设计,建筑,摄影,编程,社会制度创新与实验,经济和金融模拟等等。基本上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理科。
对于教育来说,3D虚拟世界把2D网络已经拓展的个体经验空间再次延伸。3D环境并不适合存储文字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全球各地的人,实时的以3D化的主体形式存在一个完整的虚拟空间,带来了3D虚拟化的感知,认知,心理等多方面伸延的体验。这包括在场感,分享感,沉浸感,参与感,即时合作与创造,面对面交流,虚拟物品与环境创造,可视化和社会化的体验。
与原有传统虚拟现实科技和网游3D环境不同的是,Second Life成为了一个低成本,且可以共同参与,创造和分享的3D环境。这突破了原有3D环境用于教学的诸多问题。围绕创造虚拟形象(身份),虚拟物品与环境(空间),规则(虚拟社会化),用户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上帝才有的视野和感知。
未来前景
虽然已经有如此多尝试,但虚拟世界的教育应用前景,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学习成本的问题。换句话说,是media literacy的现状。 Media Literacy是指人们使用媒体,解释和分析媒体,制作媒体的综合能力。从文本,到图片到视频,人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熟悉这些电子化的媒体。3D媒体具有更高的学习成本,掌握这些能力的人口,相比仍然是少数。
不过,从2000年前后网游全球市场快速拓展,3D虚拟环境的大众化应用到现在开始进入主流化增长。数字土著特别是在3D网游环境下成长的新一代,对于如何使用3D环境,在3D环境下从事创造,分享,社交和交流,门槛已经逐步降低了。庄秀丽老师年仅7岁的儿子,在HiPiHi世界里,可以无师自通的探索,社交和创造。
同时一项技术的采用,也依赖于制度激励与商业激励。目前在SL的众多学校,绝大部分是利用政府和非盈利机构资助的资金在进行尝试。但不是每个国家的教育机构都拥有这样的资源。相信接下来的应用,应该率先出现在降低商业成本的远程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领域。语言教育,部分职业培训是SL上已经出现的商业化应用。
需要探索者继续挖掘的是,3D环境究竟可以在哪些方面释放了人们前所未来的潜能,给学习的体验和经验带来了最大增值?如何有效的结合传统教育和基于web2.0的社会化学习?
另外,3D环境下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行为和心理问题,仍尚待研究。在这方面,硅谷的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Neek Yee,基于之前他出色的网游用户心理和行为研究,已经开始在更为开放和自由的3D虚拟世界开始了探索,其研究相当值得关注。
专栏6:界面,空间与身体:虚拟世界与体育 文/张安定(zafka)
写这期专栏时,北京奥运会已进行到第三天。我三岁的侄子正在客厅对着电视机玩Wii。这里同样是奥运赛场。他是马里奥,摇动着手柄,和一只四肢粗壮的乌龟比赛链球。链球的投掷距离,取决于手柄摇动的速度。
这个时候,真实世界的链球比赛还没有开始。新闻网页介绍北京奥运村里,不少明星运动员正操作自己的虚拟形象,在职业联赛里跟尚未谋面的对手先拼个你死我活。奥运村外,上百万的年轻人正在网吧或者家里通过电脑,跟朋友们一起组队合作,在虚拟空间奋战“街头篮球”。而在Second Life和HiPiHi这样的开放虚拟世界,居民自己建设赛场,定义项目,从自行车,跳水到百米,运动会和真实世界一样彩旗飘扬,精彩激烈。
这是我们正在体验着的奥运。虚拟空间与真实体育之间的关联,通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紧密。
早期游戏历史中的体育
自80年代中有video games以来,对体育运动的模拟就是游戏种类的一部分。我这一代,都拥有任天堂红白机的美好记忆。足球小将,世界杯足球,还有高尔夫游戏——极为简单的2D画面和粗糙的运动过程模拟,已经成为当下文艺青年们复兴的低像素美学和反智主义内容。
体育类游戏在早期属于稀缺品种。早年的技术和硬件等,并不足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身体机能模拟和身临其境。到了90年代,随着专业显卡的兴起,3D模拟成为主流。FIFA系列,NBA系列,极品飞车系列,几乎无人不晓。赛场环境,运动员虚拟身体(包括相貌在内)的逼真程度,竞技动作逼真度和细腻度,得到极大改善。
没有改变的是竞技方式)——一对一或者人与机器之间的竞技。比赛中虚拟身体的运动表现,取决于通过界面操作游戏预定技能的能力。这是一种更集中的手脑协调能力,对整个比赛的解读和阅读能力,跟真实运动需要的身体机能要求差距甚远。同时,玩家类似上帝,凭借一人之力操控全队。这样的方式更接近于即时战略游戏。
没有改变的还有玩家介入虚拟空间的方式。我们大抵都有打游戏打到手指发疼的经历。尽管游戏进化了20年,我们的身体介入虚拟空间的方式,仍然停留在键盘鼠标和或者传统手柄。
消费文化与驯服虚拟身体
真实世界的体育,是竞争性的众人游戏。竞争的对象是身体的机能,身体与精神的高度协调统一。2000年之后,当火爆的大规模多人在线网游(MMORPG)形式与体育结合时,驯服虚拟身体的旅程便正式开始了。玩家开始逐步转为运动员。也就是说,从控制一个队,到控制和培养一个虚拟身体的运动员,一个角色,并参与到群体性的竞赛中。
这样的突破也仅开始于最近两年。街头篮球,是刚开始在中国公测不久的一款韩国游戏。玩家不仅讨论真实的篮球技巧,明星,还讨论如果如何带上耳机,在听到篮球落地反弹声响的瞬间,准确的按动键盘来抓取篮板,如何以最短的时间成为各个位置上的巨星。这里的竞争,不仅是有关用苦练技能和花上货币培育虚拟身体的过程,同时也是网速,硬件等关联因素的竞争。
今年全球瞩目,仍在内测的《Empire of Sports》,把这种对虚拟身体的消费更推进了一步。虚拟身体以运动员职业历程的状态完整呈现,具有更科学和更复杂的运动技能和过程模拟。不同于以往体育类网游以开辟虚拟房间模式卸去系统和带宽负担,只能允许少数人同时在场竞技,体育帝国敞开了一个完整相连的虚拟运动社区。足球、篮球、网球、滑雪、冰撬、田径、羽毛球、高尔夫、排球、F1等等,一应俱全。全球角落的22个人,操控自己级别各异的虚拟身体同时参与一场虚拟足球赛,已经不再是梦想。
不管怎样,这种驯服具有强烈的消费文化特点。每个虚拟身体,都具有各项技能值。多项技能的相加和平衡,能决定一个角色的运动技能和水准。驯服的对象是各项身体机能的参数和指标。而实现的方式,除了通过练习游戏技能,破译游戏设计者对虚拟身体编码之外,对机能/技能符号的消费成为了最重要方式。这很直接,一定的虚拟货币可以购买到某项不需要时间练习直接获得的技能。
比驯服虚拟身体更有意义的是,玩家开始真正参与比赛。通过选择不同的角色,跟多人合作组队,第一次虚拟世界的体育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参与和狂欢状态,体育的基因开始补全。这是相对离线体育游戏的重大突破。
界面,身体与运动的虚拟未来
谈到未来,我们必须从Wii开始。过去一年多,Wii火爆全球,开启了虚拟世界与运动的另外一道大门。Wii没有炫目的3D,Wii解决的是界面,是由此通过真实身体的运动来实现对虚拟身体的运动模拟。
简单说,Wii可以把你身体的实时运动,通过手里的感应器,而不是传统的游戏手柄,直接绑定到画面中人物。力量,灵敏度,控制性等关于真实身体的指数成为了游戏的一部分。我曾经花了一个晚上,跟四个朋友一起比赛投掷飞镖。靶子是虚拟的,飞镖是手中的控制器。需要控制的是手臂的平衡,姿势,力度等。这种乐趣,操控传统的手柄,或者鼠标键盘都无法描述。任天堂推出的Wii北京奥运系列游戏,包括赛跑,跳远,链球等多种项目。这样的奥运,虽然依然虚拟,相比体育网游,已经是回归古典意义上的真实运动。
Wii同样关系身体技能的指数,不过这次是真实身体。 Wii提供了一套个人身体素质的管理系统,但对玩家而言,仿佛管理的是虚拟身体。现在,围绕Wii生产的外部设备越来越多。比如可以感应身体平衡的平衡板。站在板上,可以控制虚拟身体进行滑雪,冲浪,瑜伽等,同时也能知道今天的锻炼消耗的卡路里等指数。
在 Wii之外,Second Life这样的开放虚拟环境也在提供更多实验机会。IBM已经做了些尝试。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IBM利用真实比赛的数据在Second Life实时模拟了比赛,观众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角度来观看比赛,沉浸式的进入比赛。而Second Life的董事,莲花软件的创始人Mitch Kaper最近迷恋上了3D摄像头,利用真实世界身体的直接动作,而不是通过鼠标等,来控制虚拟世界身体的运动。
所有这些,都将推进界面的改进,塑造身体与虚拟空间的新关系。可以想象,随着处理器,图形渲染能力,带宽等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部设备,可以胜任实时跟踪和处理人的运动信息。也许在某天,人们可以实现虚拟的同场竞技,而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同样的沉浸式的外部设备,参与到虚拟的奥运盛会中。
专栏7:虚拟盛宴与拟像社会 文 / Zafka (张安定)
再过一个月,全球虚拟世界大会从纽约移师伦敦。大会的主题是“媒介和沟通的未来(The Futur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从商业角度看,主题切合目前虚拟世界行业的热点。已经启动的消费者市场和企业市场,焦点正集中在虚拟世界的媒介和沟通特质。
这是个信号,虽然行业仍在早期,主流消费主义力量已经开始杀入这个世界。从鲍德里亚的理论推断,作为仿真新形式的虚拟世界的繁荣,将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拟像社会的出现。这不是麦克卢汉温情主义的地球村,而可能是鲍德里亚式的现实的荒漠——自我生产实现的虚拟世界谋杀了真实世界。
当然,相比传统大众媒体操控的人口,虚拟世界仍然是在起步阶段。不过,仍可以探讨,虚拟世界作为一种新媒介,到底意味着鲍德里亚眼中拟像的登峰造极,还是能带来主体塑造和主体间交往解放性的意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在媒介形式之外,重新回到媒介内容和生产方式。虚拟世界的拟像,直接体现为日益繁荣的虚拟物品。初步的讨论可以从虚拟物品的生产开始。
符码的全球贸易:幻想王国的耕作
网游作为虚拟世界的实践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这些世界,绝大部分都是幻想王国(fantasy worlds)。网游是一种符码即产品的商品,但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它无需通过传统大众媒介的仿真来兜售,它自身就是拟像。设计虚拟世界——从人物,服饰,装备,情节到规则,就是生产完整虚拟物品/符码的过程。 网游不仅仿真全新的个体身份,还生成了封闭体系的虚拟世界拟像。
所有这些都只是数据库里分类存放的数字符码,但拟像是超真实的。它就是现实,有自己独立的生长逻辑。对于类似魔兽世界的传统网游开发运营商来说,固有商业模式是推出整个虚拟世界作为完整的符码系统被消费。但从一开始,符码的消费就被拆分。虚拟物品以一种人人皆可消费的小额形式,把消费主义原则渗透到了真实生活的每个角落,以低廉的成本更好的制造和满足需求。
拟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中国昏暗的网吧和工作室里,金币农夫们24小时不间断生产虚拟物品和虚拟货币。这是符码的全球贸易。大量虚拟装备和货币的全球交易,自我维持了拟像,并对真实世界施加了影响。
全球的网游死硬粉丝们,按照《黑客帝国》的台词描述,“一直生活在鲍德里亚的图景中,在地图里,而非大地上。”当他们来到大地,新闻和报纸屡屡报道,很多人丧失对于真实社会的感知,犯下了“完美的罪行”。
某种程度上,作为网游的虚拟世界仍属于传统大众媒体的类别——游戏设计师和商业力量主宰了世界的样式,个体游荡在媒介生产的拟像中。
传统媒体的虚拟世界:大众消费时代来临
最近几年,在网游之外,以社交娱乐为核心的图形化虚拟世界(更准确说是虚拟社区),通过联通真实商品世界,已经开始推动拟像的大规模生产,把虚拟世界这一媒介拓展到全球更多人口。
目前业界红得发烫的全球儿童和青少年虚拟世界,盈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就是出售虚拟物品。身体,衣服,房间,家具等各种虚拟物品的交易异常火爆。不同于网游的幻想王国,真实商品开始以虚拟物品的形态出现。
未来几年,虚拟世界还将见证拟像的大规模生产。MTV,迪斯尼,芭比娃娃等传统媒体和商品的进入,已经开始带来传统内容和服务的直接符码化。虚拟世界的头号服务商Millions of Us,前不久得到娱乐公司授权,可以把众多明星的形象再次虚拟化出售。在消费主义更为旺盛的中国,腾讯QQ目前占据了年虚拟物品出售额的全球首位 。
这样的虚拟世界,与网游一样仍属于传统大众媒体类别。全面模拟真实世界,拟像的生产,仍控制在资本手中。从消费社会的经验来看,生产和售卖虚拟物品的商业模式,因为其符码注定的消费主义基础,注定成功。
虚拟世界新媒介:交流还是眩晕
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介在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把互动通通内爆为一个平面,一个屏幕,一个窗口,一个单向度的时空现实。这样的后果是社会交往和社会价值的瓦解,拟像客体占据了统治。也即鲍德里亚所言,我们“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现实的交流,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
如果对虚拟世界的分析停留在这里,鲍德里亚的幽灵仍然存活。鲍德里亚的分析,基于传统的大众媒介和早期web1.0时代的互联网。这些媒介最大的缺点在于单向性和可深度交互性的缺失。此种情形下,资本控制的大众媒体,很难实现由生产者和受众,技术与文化共同建构的历史进程。拟像也就无可避免的成了一种独立于交往主体的客观存在。鲍德里亚的推演里,面对拟像社会,逃避,沉默和不在场是最佳的办法。
但互联网作为媒介的解放性作用才刚开始。Web2.0时代是一个社会化媒介的时代,资本操控的符码生产体系正面临来自个体和群体的自我表达的挑战。虚拟世界的2.0时代,也就是作为新媒介的年代同样已经来临。大众可以自由创造和表达的Second Life,HiPiHi,还有OpenSim开源平台,都具有了传统媒介所不具有的特点。 这包括我已经在之前的数篇专栏论述过的完整主体身份和完整空间概念的出现。
数字媒介已经充当了主体间交往方式之一。一个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虚拟世界平台,一个人人可自主生产的媒介和交往平台,对于拟像社会的个体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更多的深入讨论,仍需要通过持续的数字空间人类学,结合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考究,跟随虚拟世界的成熟展开。我也将在今后的专栏里继续关注。
专栏8:水下社区,风暴美学与虚拟世界再实践 文 / 张安定(Zafka)
刚过去的周末,我参加了第二届eARTS上海电子艺术节的“风•水全知”浦东户外跨界展演。演出很特别,HiPiHi虚拟世界居民创建的3D在线水下社区,投射在露天的360度巨型环幕,远处高楼环绕,我顶着星空现场配乐。
演完回到北京,收到了曹斐的Email。她在Second Life上庞大的RMB City计划,11月参加美国新奥尔良的国际双年展。RMB City的领地里,已经虚拟了三年前新奥尔良城市遭受飓风灾难的现场一角,很快就要邀请世界各地居民访问。
又一次巧合。几个月前的一次专栏,我曾谈到过虚拟实践的意义。当时写到了曹斐的RMB City作为艺术家的社会实践和实验,对比HiPiHi居民的原点镇计划作为草根Netizen的自主实践。现在,两者的话题同时与环境有关。
风•水全知
应该说演出的场地破费心思。上海科技馆旁边自然形成的湿地旁,露天搭建了一个高15米,直径30米的户外 360度全景视频墙,作为大型视频音频装置与现场演出平台。策展方希望利用大型全景视频墙的放大效果,唤醒观众的生态环境建设意识,呼吁更多城市“生态风景”的回归。
重头仍然是传统的新媒体互动艺术领域作品。龙二使用微型摄像机拍摄附近湿地的水下风景,再投射到环幕,现场实时调制,和音乐互动。Carl-Emil Carlsen使用风速仪,把自然界风的信号转换成现场演奏的声响和音乐符号。冰岛的Kira Kira在夜晚放飞了风筝,采集高空的气流与地面的演出相映成趣。观众躺在场地中央的垫子上,可以仰望星空和环幕。
HiPiHi居民应邀参加这次艺术节,基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思考,创作了未来水下社区。在我演出的时候,观众正在舞台下操控电脑,骑着鲨鱼,呆着头盔,或者有些嘲讽的骑着汽油桶,腰里别着二锅头,在线上的水下世界穿梭。水下世界里面,有未来已经被淹没的东方明珠的遗迹,还有纪念博物馆。当然也有对应水下生活的未来风格的新生存空间。环幕外的现实世界,周遭是高楼,仅存的湿地,看不到星星的星空,还有高楼间穿梭而过的晚风。观众就在虚拟和现实之间。
应该说水下社区的设计和修建具有相当的水准。边演出边注视环幕,我甚至怀疑这是某部未来科幻片拍摄完成后遗留的高昂造价的场景,或是后期剪辑过的影片片段。HiPiHi居民上星空,玄氏,天才还有sna_rv4,算得上是中国虚拟世界诞生的第一批居民艺术家。
在创作完水下社区之后,上星空在论坛里写了个帖子,完整了想象和阐述环境恶化与水下社区。这是虚拟世界居民关于环境变暖与人类生存的虚拟实践。我摘录一段如下:“变暖得气候摧残着地球极地的冰雪,我们的圣洁世界已经只能流传于影像之中。过程是缓慢的,结果是残酷的,无数的人们抛弃了自己的家园走向曾经望而生畏得高原,但是水面不会再次升高么,谁都不知道。终究还是有人不会屈服,他们开始适应水下生存,开始建设水下社区,开始倡议人类全力保护环境。重新生活在地面上将一直是他们得梦想,恢复地球的水陆比例是他们研究的课题。”
新奥尔良风暴美学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2005年飓风登陆美国新奥尔良造成的悲剧。今年3月,曹斐应展览策划人邀请访问新奥尔良。在她的博客中,曹斐拍摄和描述了仍在废弃中的家园,一个仍然待建的鬼城,还包括一些惊心动魄的细节。2005年飓风之后,展览希望重新定位新奥尔良作为文化之城,期待艺术在这座城市的大规模展现,带动城市的复生。
这次曹斐和Map office合作的虚拟新奥尔良,在RMB City城市一角,以一种素描笔触,极简的黑白风格塑造。”What Happens Here, Stays Here”是作品的标语。每隔两分钟,通过脚本,程序启动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洪水来袭。同时房屋和树木倒塌。现场还有跟新奥尔良密切相关的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脚本,可以自动跟随访问者移动。例如来自新奥尔良的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人Oprah Winfrey。飓风之后,她赞助了1000万美元给居民修建新居。还有目前红极一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作为黑人,他在新奥尔良也被看成是希望所在。
登陆进入,首先触动我的是颜色的对比。场景如同记忆,而每一个在线重新进入这个记忆深处的虚拟形象,是现场唯一的彩色。也就是生命的痕迹。这是基于记忆的抽象剧场。打破了时空,冷静不着痕迹,但也留下了温暖的出口。
剧场与记忆
某种程度上来说,HiPiHi居民的水下社区和曹斐的新奥尔良,又一次同样点击了相似的话题。越来越多人开始通过虚拟世界的实践,对人类身边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模拟,试图形成公众的集体认知,寻找超越之道。以前我曾经写过Second Life中的艾滋病防治协会活动,还有虚拟世界居民反对法国左派总统获选人勒庞的虚拟社会运动。
3D虚拟世界对时空的整体操控能力,远超过2D网络。这使得人类的集体记忆投射和集体认知想象,寻找到了一种新的手段。对于记忆来说,这是一种不可以经历的重新经历。曾经发生的现场可以变成人人参与的剧场。对于想象来说,这是未曾经历的正在经历。理性与狂欢并存。就环境问题而言,曹斐的虚拟新奥尔良把灾难的自然逻辑和政治与经济逻辑,抽象而富有美感的混合在一起。用这样的形式,集合公众,来重新认知和反思环境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是电影或者其他视觉艺术能做到的。
从安舍钟登陆商业周刊封面算起,虚拟世界的第一个全球浪潮其实已经过去。眼下在伦敦,刚结束两个全球虚拟世界大会。产业的成长,商业化的应用,仍然需要时间。但是对于虚拟世界平台的社会性和艺术性应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对3D虚拟世界的早期使用者(early-adopters)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其无所不能的创造力和自由度。冲击由此产生,被虚拟世界改变的现实认知和现实本身,才刚刚开始。
新奥尔良的双年展11月1日开幕。远在中国的我们可以登陆Second Life,和新奥尔良的人们一起重新经历过去和展望这个城市的未来。我在想,针对已经过去的5.12地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用一些别样的形式,来重新塑造我们的记忆和想象。
2022.04.04
2007 ”第二人生音景“项目 – “虚拟世界的实地录音”
过度符号化的现实:虚拟世界的实地录音 文 / Zafka
过去半年,我和Zafka Ziemia(我的avatar)断断续续的在Second Life(简称SL)旅行。这是一个居民数目不断增长,可以自主创造的3D在线虚拟世界。我喜欢SL,也相信虚拟世界很快会成为人们生存的另一个重要空间。因此,在探索这个世界的同时,我开始用Audio Hijack取代麦克风进行field recording,试图留下关于虚拟世界的第一份声响记忆。
在SL,土地拥有者们可以实时播放音乐,将网络电台在三维空间剧场化。关闭音乐,在大部分场合,你能听到SL提供并预置的风声,脚步声,虫叫声,海浪声等自然声响,还有居民上传的声响片段。它们通过网络实时下载并自动重复(loop)播放。这些音质高低不一,采自真实世界的短促声响片段(SL规定每个sample不超过10秒),混合着客户端界面操作声,构成了虚拟世界的音景(soundscape)。
虽然可以上传声音片段,整个音景中少有居民精心架构声响环境,也少有工业声响。海浪声,水流声,风声,篝火声,鸟鸣,虫叫——几乎无所不在,但几无变化。真实世界中被工业社会遮蔽的自然环境声响,在虚拟世界通过预置的循环播放被过分强调,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过度的自我救赎。这些被“过分标识”自然声响,还有风铃声,关门声,叫喊声,机械声等居民上传的声音,都在重复播放中反复指向人们的真实声响记忆。即使如此,因为去掉了真实世界声响的多样复杂,相互联系和层次,虚拟世界的声响环境听起来并不真实,倾向于一种廉价的抽象。有的时候,由于网络带宽速度,电脑配置的限制,也可能导致声响的延缓,停顿和变形,最终强化音景的机械,重复,突兀和笨拙。
SL是无法自主发声的乌托邦。它复制了真实世界——视觉,空间连同情感,但没有也无法复制真实世界的有机声响环境。不过,很多时候,正是对包括话语在内的大量真实世界声音的舍弃,已有声响的不断loop,让我感到一种抽离,一种虚拟空间中沉浸式(immersion)的体验。不可否认,avatar行走和飞行的声音,还有聊天时不间断的键盘打字声,客户端界面操作的声音,都成为了个体行为可感知的声响,标识了个人在虚拟空间的存在。而在真实世界,人们被各种嘈杂的工业声响包围,个体行为的声响已经很难被自主聆听,并成为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方式。
不过,在虚拟世界,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声响层面早早被剥离了。也许这里根本不需要声音。事实上,很多居民已经选择关掉所有界面操作声和预置自然声响。虚拟的化身可以飞行,可以转动鼠标以鹰的视野查看空间结构。人们不需要聆听空间内的声响来感知环境,辨识方位。大部分地方也没有建立声音的辨识体系。虚拟世界比真实世界更为视觉中心主义。真实个体在虚拟世界的存在,是通过操控电脑,以凝视3D化身的方法实现。
虽然很快SL就将全面实现语音聊天,但我仍会选择打字,聆听键盘的声音,清晰的告诉自己——虚拟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接口,是一套冰冷的设备。在键盘的另一端,虚拟世界并没有新鲜的空气。那是生命和声音的真正母体。
An Over-symbolized Reality: Field Recording in the Virtual World (By Zafka)
I’ve been traveling on and off with Zafka Ziemia (my avatar) in Second Life for the past six months. It’s an online ‘metaverse’ whose increasing ‘residents’ can create 3D virtual world of their own. I like Second Lif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virtual world would soon become another essential space in people’s life. Therefore, as an attempt to collect the first sonic memories of the virtual land, I began to do field recording in it (using the Audio Hijack software as microphone).
Land owners in Second Life can play live music and expand online radio into 3D theatre. Shut down the music and you’ll hear the pre-recorded sounds in the Second Life client software, including built-in natural sounds (wind, footstep, insect, ocean wave, etc.) and sonic fragments uploaded by the residents. Streamed in realtime and looped, these sounds of various qualities are sampled from the real world and are limited to no longer than ten seconds each. Together with the operational sounds of the client programme, they comprise the virtual soundscape of Second Life.
The sound uploading feature has not, however, resulted in much resident-made sonic environment, nor is there much industrial sounds. The sound of ocean wave, torrent, wind, fire, bird and insect are almost everywhere, but with little variety. Masked by the industrial sounds in the real world, natural sounds are over-emphasized as unconscious, excessive self-salvation in the virtual one through looping. These ‘over-symbolized’ sounds, as well as fragments uploaded by residents (wind-bell, door, yelling, mechanics, etc.), speak to people’s memories of real world sounds through endless repeating. Yet they don’t sound ‘real’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omplexity, inter-relationship and multi-layered construction. In fact there is a sense of cheap abstraction in them. Sometimes sounds would be delayed, paused or morphed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bandwidth and computer system resources, thus stressing the mechanical, repetitive, and clumsy quality of the soundscape.
Second Life is an utopia deprived of the capability of sound making. It replicated the visual, spat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of the real world, but left out the organic sonic environment of it. In many occasions, however, it’s precisely the abandon of real world sounds (including voice) and the looping of sounds at hand that bring us the detachment and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in the virtual space. The sound of avatars walking and flying, the constant typing sound while chatting, and the default operational sound of the Second Life client are no doubt recognizable to individuals and thus reiterate our existence in the virtual space. Plagued by the noisy industrial sound of the real world, we find it difficult to engage ourselves in an active-listening relation with daily sounds of human behaviour, which would have been an important way of self-perception.
Yet human beings have long been detached from the environment in the virtual world when sound is concerned. Perhaps sound is not necessary here. Actually, many residents have chosen to shut down all the pre-recorded sounds in and of the client software. Avatars can fly, and you can control them to observe spatial structure in bird’s eye view. People can detect their environment and tell direction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aural sense. With sonic recognition system absent in most of the places, it turns out that the virtual world is more visual-centric than the real one.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virtual space depends on gazing at the 3D avatar through man-machine interface.
Although voice chatting is on its way to Second Life, I think I’m gonna stick to typing and to the sound of keyboard. I need to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world is this lifeless interface, and that fresh air – the essential embryo of life and sound – is absent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keyboard.
(Translated by Lawrence R.Y. Li.)
2022.04.01
2007 “青海”项目 – “在”青海:现场即剧场
现场,不能被想象。在青海,我们双脚在地,头顶着天,打开所有感官去聆听。我们知晓当地声响环境的丰富,多样,独特和流动。我们和人群,空间,声响和社会情境在一起。
现场,有关存在和参与。我们知道这是随时消失的现场。现场即剧场。在青海,我们是游客,观众,也是场中人。回到北京和广州,当我们回放几十个小时的青海录音,很多声响正在千里外重复,变化,消失。我们永远赶不上,但我们曾经在,我们仍有机会表达。
现场,与意图有关。在青海,我们思考聆听对象和聆听行为。我们实践行动录音与声响即兴写作,尝试重塑声响-影像-认知之间的关联。
不在青海:悬浮景观与城市微观声响地理
西方当代艺术中,声音艺术更多以装置形态进入到美术馆体制。声响被看成是自然和科技的产物,被看成是通过一些界面和机制重塑,以不同方式在空间和观众互动。这是一种相当程度剥离了声响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聆听可能,剥离了声音本体时间线性,归属于当下美术馆体制的声音艺术。
我们实践实地录音(field recording) 。正如姚大钧所说,中国的激进实地录音艺术,是一种反唯物主义,反自然音景的极端人本主义取向与文化关注。作为研究辅助性资料,人类学研究者曾录音记录不同种族的丧葬祭祀,音乐舞蹈,民族语言等。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基于对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声响同质化反思,强调对文化的保存,主张声响生态学意义上的实地录音,带来了大量反工业化的自然音景。
但剧烈变迁的中国有不同的景象。过去多年,姚大钧的中国声音小组,倡导关切中国人文环境和人本声音实体,关注公共空间,私密空间和内在空间的声音现象,对各地的声音实体进行监听/采集/整理/分析/保存/解构,以及重新语境化,同时高度尊重声音本体。
三年前,钟敏杰,林志英,陈钢,覃岛和我以21楼的名义,在广州沙面惊艳会K歌会所——一个特定的无差别城市内部空间,定制邀请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参与聚会,以实地录音和影像,将广州城市空间的物理、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复构性,再次浓缩释放。之后,我去了北京。21楼还未曾来得及按照设想,在网吧和教堂等再次实现我们的空间复构与穿越计划。
敏杰和阿英拿起麦克风继续穿行在广州大街小巷。他们发表合作双唱片《悬浮景观》, 观念兼顾声音本体,抽象而细微,呈现流动的,不断重构的城市空间声响和人本声响。07年开始,他们以“PlayBackUnit”(拍背有理)两人组形式,高频率的在城市进行日常声响游击战,持续用blog释放对城市的日常聆听。
同时,过去两年我探索“听不见的城市”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权力与资本逻辑,在实地录音实践中梳理城市物理和社会空间的变迁,寻找城市声响构建的历史谱系。07年,从雍和计划到大声展的RYC计划,我又试图将这种城市声响的政治学聆听路径,转换为城市微观声响地理实践——行走/研究/听音,通过微观的地点(place)与空间(space)的融合,触及情感与记忆,将宏大逻辑转化为众人可参与的日常实践,转变为公共平台可分享和探讨的话题,并最终成为批判的力量。
在青海:行动录音与声响即兴写作
在青海,我们重新聚集。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秉持但不坚守宏观分析逻辑。我们相信,任何现场,即是剧场。当我们开始介入,无论使用什么媒介,我们便在剧场之内。我们参与剧场。我们主张观念性的行走与聆听实践。我们称之为行动录音。从学术角度来说,行动录音的实践规则,倾向人类学,观念考察则多以社会学和政治学为支撑。
实地录音也叫Phonography, 希腊语,意为声响写作(sound writing)。我们把行动录音,视作即兴的声响写作。剧场具有宏观的可预见性,类型性,但更充满偶发性,事件性,不可复制性。我们闯入了当地,在地的进行声响写作。这类似一种快速的素描。
在青海,我们走过玉树,西宁,还有格尔木。我们去过盐湖,戈壁,牧场,黄河,我们跟自然一起。我们还穿越街道,公路,公园,集市,学校,商店,广场,火车站,清真寺,佛教寺庙,毡房,我们跟人群在一起。
在青海,我们观察,抽取,记录。割裂某些东西,抽象某些东西,又去掉某些东西。我们关注个体和群体在空间的流动,聚集或分散的发声。行动录音涉及大量个体语言。混杂的藏语,青海话和普通话。人的语言和行为,产生了大量具有情感的,个体对社会想象的声响。这些声响具有不可复制的剧场感。
我们考察人本发声的社会情境,空间环境,情绪状态。我们聆听情绪,聆听个体表达,集体想象和隐藏的秩序。 我们聆听不同语言之间的合唱与差异,聆听隐藏的权力秩序。 我们体会海拔高度,空间环境和声响密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公共空间流连转换,尾随人群,不断游击。
这是剧场,我们在其中,参与其中,同时随时准备介入与激发。有时候,我们直接参与场景。 在塔尔寺,我们组织一群导游,割断场景与个体发声,聆听导游的语系与个体想象。有时候,我们默不做声,设定距离,动作,关系,成为现场的一部分,成为声响生产的诱因。有时候,我们提问,设问, 攀谈,引诱, 解释,反抗,激发,直接成为声响的一部分。
在青海:声响,影像与认知
声响的聆听,长久的历史是脱离视觉环境,脱离可见的社会情境。我们想探讨,如何驾驭社会性的声响,有效呈现我们的观念和体验?我们尊重语言作为声响的独特性。我们意图记录和表达——那些有意识/无意识的个体/群体声响,视觉化情境,大脑深处不言的理性逻辑,三者之间如何相互融合,斗争,穿越黑暗悠长的隧道。
青海之前,钟敏杰和林志英的“拍背有理”blog,以“标题-图片-声音”格式,构成了每次作品/帖子发布的规则。这是一种意图重构的视觉-听觉-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在RYC的展览,我也曾试图在一个封闭空间,以无声的方式,重建文字,声响想象与个体记忆间的关系。
但在青海,我们重新用声音思考,尝试重建声响-影像-认知间的关系,寻找一种方法,在离开剧场时,仍可表达和再生产我们在场的复杂感受。
我们动用了除麦克风之外的媒介——数码相机,DV。我们不在乎作品是否是装置,是否是唱片,是否是录像。我们在乎:这是否可感知,是否可聆听,是否来自内心。我们呈现给你们,我们捕捉到,我们即兴写作过的,我们参与过的,青海。
“一切声响,都是欲望。 寂静,无法捕捉。” 我们还想回到青海。 去现场,在现场,不断回到现场。回到那里,在广场游荡,在戈壁滩发呆,一起探讨,有关鸟的问题。
2022.04.04
2007 “青海“项目 – 青海日记
“一切的声响,都是欲望。 寂静,无法捕捉。”
西宁南山公园(7月8日)
巨大的party。Woodstock的西宁版本。直射的太阳让人头晕脑涨。
中央舞台上,是西部五省的花儿歌手。字正腔圆。外围的是老年人合成团,他们对歌,他们伴奏,他们唱。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老者。在最外围,有羞涩的歌者。他们无人围观。他们围坐着,啤酒,遮阳伞。他们的花儿属于这个下午。
循化(7月9日)
安静。让人不知所措。这是一个小县城。就在两座山的中间。县宾馆的门口,悬挂着长长的风车。从一端到另外一端,随着风,随着树叶,噼里啪啦。小小的广场上,所有声响都是你曾听过,曾经熟知的。不同的是分贝,是在地理空间内的反射。
黄河边,水势看似平稳。吊桥上年轻人悬空而坐。风扫垂柳。
塔尔寺(7月10日)
西宁小雨。阴冷。塔尔寺的游人稀稀拉拉。我顺着山势,一个殿接着一个殿。尾随人群。倾听。
恰逢法事。这是一个游乐场。络绎不绝的旅行团。所有的导游都在重复一样的话语。语气,节奏,设问,反问,衔接。天衣无缝。
朝拜的人无声,喇嘛无声。只有导游,是这个空间最大的声响。话语是一种建筑。有人试图用话语重建历史。有藏族的导游,有汉族的当地导游,还有一些说英文的导游。
声音和声音之间的空隙,比我所经历的要大得多。我似乎习惯了都市延绵的巨大的声响。现在的敞开和宁静,开始让我不知所措。总想捕捉点什么。但似乎什么都捉不到。
格尔木第一日(7月11日)寂静无声
12个小时。到达格尔木东站。头部血管开始有些压力。去往拉萨的火车开始供氧。天寒。风大。清晨7点,站台是空旷的。一切都是平的。没法想象如此平坦的高原。火车是这个土地上最直的直线。远处进站的火车冒出一股浓烟,阿英冲过去举手就拍。极似某科幻片场景。
我们是仅有的三个出站者。如今大部分人留在了去往拉萨的火车里。曾经繁华的格尔木安静得让人不知所措。买了回程票。敏杰和阿英在火车站大厅台阶处录音。一声汽笛,椭圆形分布的站外建筑,逐个把汽笛声传递。让人想起在循化,小小的县城就在群山之间,所有的声响,都自己应答。
吃过早饭之后。直接包车前往盐湖。崔师傅是盐湖某分公司的职工。二十多年,如今靠包车旅游过活。他的绝活是把人直接带到盐湖集团里面。
面对盐湖如同面对一场魔法。土地,湖水,矿物质,高原直射的阳光,风。混杂了盐结晶的土地坚硬无比。整个盐湖被分割成2公里乘以2公里大小的池子。采收船就在湖里。我听见风声,盐湖拍打着人工堤岸,脚踩在盐土地上,咔咔作响。
崔师傅的车开得极快。通往胡杨林的公路远处,水汽升腾,海市蜃楼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仍然无法相信地理上的平坦。至少在我的视野和脑力可想象的范围内,这是对一望无际的最佳解释。车辆碾过公路的声响,就是电锯锯开地理的过程。
车停在路边。寂静无声。这是对听觉的最大挑战。风轻的时刻,即时把录音电平开到最大,也只能听到苍蝇蚊虫的声音。远处公路上疾驰的车辆,如同天空高出的飞机。空荡的,贴着地面的回声。
闯过干涸的湖面,戈壁里蚊虫猖獗得很。爬过沙丘,远眺。这就是青海。这个省的大部分区域,也是如此的声场。寂静无声。我们三个坐在沙丘上。沉默无语。我让麦克风自己躺在沙丘上工作。今天无风,这似乎让人很绝望。
我想起北京,广州,上海,想起西宁。这些都市的声响,具有类型学的相似性。差别的只是分贝。而面对荒无人烟的戈壁,草地,面对自然的声响。只有寂静无声。人类的欲望,是最大的声响。
格尔木第一日:广场(7月11日)
这是来青海以后最令人激动的时刻。7点10分开始。我们三个从宾馆出发。格尔木突然热闹起来。广场是一个城市最奇妙的地方。我见过很多二三级城市的广场,但还没有见过像格尔木这样的。
每个点,桌球厅,练武人群,舞蹈者,露天卡拉OK。
五年前,广场上跳藏族舞蹈的人,围观的人,比现在多上至少三倍。青藏铁路大军已经离去。一个饭店过去一天的营业额是800-1000,现在只有200-300。跳舞的都是年轻人。
一个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广场到底意味着什么?西宁也是在最近五年发展起来的。两个广场堪称某种奇迹。
格尔木第二日(7月12日)
仍旧在格尔木市区转悠。风大。广场附近的公园里,胡杨林高耸。开阔的地理环境,广场式的混响。树叶在头顶沙沙作响。
西宁(7月13日)行动录音
今天晚饭,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讨论。核心话题:行动录音。最近几天的录音,让我更明白了敏杰和阿英过去两年执着的“拍背有理”项目背后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我过去两年所走过的城市微观声响地理路径,或者说所谓城市声响的政治学聆听,最终都走向了行动录音。
2022.04.10
2007 “RYC 尚◎都”项目 – 一次城市微观声响地理实践
文 / Zafka
RYC, 意为“Reinvent Your City”——重建你的城市。这是一个来自民间团体的初次行动。行走/研究/听音——我们试图理解日常的声响,更试图理解所生活的城市。我们相信,一种 来自实践,来自双脚和双耳的活动,可以还原城市声响的情感和心理感知,重建属于耳和心的意象城市,更就此打开批判与建设的新空间。
过去两年,实地录音在中国的兴起,已经从将艺术家私人对城市声响的记忆,通过唱片/在线播放/演出等形式,转变为有限大众的部分集体记忆。过去两年,我也曾连续撰文书写“听不见的城市”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权力与资本逻辑,试图通过梳理城市物理和社会空间的变迁,寻找城市声响构建的历史谱系。
但脱离了具体时空背景的城市声响,以各种形式回到人们耳中时,声响本体的先觉性和优先性,已经模糊了其中主体可能的社会批判能力。基于声音艺术本身的声响准则,无法沟通听觉之外更为深刻的命题。公共城市声响,因为听觉的公共性与日常性而被漠视,可能的秘密仍然停留在艺术家的私密舞台,而无法在公共平台进行交流和探讨。而我所尝试的宏观层面声响环境构成的学术探讨,在我包括《雍◎和》等已完成作品中,因为缺乏更为细致的整套方法,也无法摆脱过度私人化,并完成从理论到实践与表达的最终过渡。
我试图做些改变:通过RYC团队,将城市声响政治学聆听的路径,转换为城市微观声响地理的实践,一种可分享的实践。行走/研究/听音,与城市中的同伴一起,从每一条街道开始,通过微观的地点(place)与空间(space)的融合,揣摩理解每一个声响,触及情感与记忆,并由此尝试建立一套方法,将宏大的逻辑转化为日常的实践,转变为公共平台上可供分享和探讨的话题,并最终成为批判的力量。我期待团体的每一个成员,从声响入手,最终将可以独立在城市中聆听并反思,在每一次实践中,发展出城市声响的游击战,并最终超越声响,达到声响反思的个体生存层面。聆听,原本私密,但从来都是抵达公共的彼岸。
鉴于以上考虑,RYC团队的成员都从网上招募。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都是城市的普通一员。RYC团队的首次实践,以大声展SOHO尚都为出发点,行走区域东至东大桥路东侧,北至芳草地社区和三丰里社区,南至光华路,西至雅宝路。我们花了两个月,每个周末在一起,一起学习sound walking,学习实地录音,研究行走之处的城市微观地理,体会声响本体与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关联,看看政治权力与资本的逻辑如何改变城市的一砖一瓦,改变人们脸上的喜怒哀乐,并塑造了当下的城市声响。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将个体的声响记忆转化为批判,学习提出问题,并转化为作品的呈现。
这次RYC首次实践展览呈现的,有手绘的微观地图,有声响地点的研究,有实地录音,还有录像,装置等作品。RYC试图表达对城市声响的私人记忆/想像/认知,表达聆听和生存者的复杂情感,链接个体-聆听-城市三者之间的联系。而每个成员爆发出来的能力,已经说明在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个体日常表达的手段。
如果RYC的城市微观声响地理,可以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声响自由实践,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我们也希望,RYC团体的实践,还将有下一次,再下一次。
2022.04.04
2007 “雍和”项目 – 魔幻大街
“雍◎和”——魔幻大街 文 / Zafka
2006年末,我从广州移居北京。我曾说,城市声响(Urban Soundscape)已经是城市正义与否的标注。我还惦记着广州的“不干净”—— 过去二十多年民间资本和移民的主导下,广州城市空间斑斓无序,声响纷繁芜杂,没有城市规划理性主义的政治洁净幻想。
相比广州,北京要“干净”得多——马路宽广笔直,全球同质的交通声响干净有力,无处不在。这个古老的都城,城市空间布局和声响环境从来都是政治秩序最现实和直接的投影。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但政治合流资本已经是城市变迁的主导力量,加速将北京的城市发展引向“断裂”——社会整体规划与文化保存,个体物质生存发展与心理情感沉淀之间的断裂。
我挑选了雍和宫——一个我过去多年造访北京最多的区域,试图聆听并找寻这种断裂的细微之处。雍和宫位于北京二环东北角,附近有国子监,孔庙,以及众多老北京胡同。这个区域不仅是北京传统城市声响的积淀之地,所处位置更是寸土寸金。过去两年,为了迎接奥运,也为了发展经济,雍和宫附近胡同已经陆续拆迁和改建。
从听觉上来说,南北走向的雍和宫大街是这个区域的“魔幻大街”,是这个城市发展断裂的最佳注脚——选择东西双向任何一个胡同入口,往里行走10-15米,雍和宫大街嘈杂异常的交通和商业声响,转眼转换为安静平和。这是一个狭窄地理空间内剧烈转换的城市声响环境。狭窄的胡同,前工业时代城市声响的生产轴心,如今成为了对付嘈杂交通声响环境最有力的“消声器”。
同时,胡同的狭窄造就了不同于雍和宫大街的商业和社区形态,也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声响环境。胡同中最多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三轮车,承担了大部分日常交通和商业功能(上下班,送啤酒,杂货,收破烂,送报等),构成了声响环境的主体。另外,胡同也是传统的社区空间。胡同的公共声响,部分重叠了居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声响——小孩嬉闹,大人呵斥,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等。
但这里是资本的低地,也是城市生活的低地。我喜爱胡同的宁静,却无法假设自己也如同这胡同中的大部分群体一样生活困窘。雍和宫区域胡同里的人们,并不如人们想象那样怀旧。很多人期待离开狭窄破旧的胡同,而他们的居所,正处于政府规划地图上保护区域的标尺之内。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孤岛,日子一天天过去,对他们来说,胡同声响的安宁已经过于廉价。而在这个城市,还有不少这样的魔幻大街。我只能多次行走在雍和宫大街和它附近的胡同,用耳机和麦克风,试图理解这段城市微观地理变迁的历史。
仍需要一些反思。已经有太多对城市断裂性变迁的批判,蜕变为不负责任的怀旧主义情调,进而演变为绝缘冷酷高高在上的道德主义。我无法埋怨在大部分人长长的城市生存需求列表上,声响环境可能只是最后一项。城市声响环境重建的未来,只有建立在城市发展本身的正义之上。这样的正义在于,在资本试图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横行摧毁一切时,更为深刻的政治和文化逻辑可以唤醒,可以拯救与平衡,并在让人们在自主决定自身和城市发展方向的同时,提供更为前瞻性的考量,避免发展的断裂。
事实是,一个高速变迁城市的断裂,并不只是资本和政治的简单合谋。这不是故事的全貌。每个人都是城市变化的参与者,每个人都在矛盾中度日。作为这个城市新的定居者,我所能书写的,只是一副私人城市声响地图和一张唱片,把我用脚和耳朵丈量过的地方,用一套城市微观声响地理的方法,从我的情感和体验出发,以回忆和想象——一种并不确定性的东西,把关于魔幻大街的一些,简单记载下来。我只是有些担心,那些被忘却的城市声响——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的,情感的,心理的,那些基于个体对自己生长的城市认知和心理的断裂,才是城市变迁断裂的最细微致命之处。我期待未来,我能听到城市声响庇护着正义,我不在乎声响是否新旧,分贝是否高低。因为那些耳朵,终究会被唤醒。
注:
● 雍
◎ 和谐。
◎ 古同“壅”,遮蔽,壅塞。
◎ 古同“拥”,拥有。
● 和
◎ 相安,谐调。
◎ 平静。
“Yong ◎ He” – The Magic Street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I moved from Guangzhou to Beijing. I once said that urban soundscape is already an indicator of urban justice. I love the “uncleanness” of Guangzhou. Under the dominance of private capital and immigrant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urban space of Guangzhou is colorful and disorderly, and there is no illusion of political cleanliness of urban planning rationalism.
Compared with Guangzhou, Beijing is much “cleaner”. The roads are wide and straight, and the global homogeneous traffic sounds are clean and powerful, everywhere. In this ancient capital, the urban spatial layout and acoustic environment have always been the most realistic and direct projections of political order. The tradition continues to today, but the co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capital power,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ce in urban change, accelerating Beijing’s urban development to “fracture”-the rift between overall social planning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individual materi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precipitation .
I chose the Lama Temple, an area I have visited the most in Beijing in the past years, trying to listen to and find the subtleties of this fracture. The Lama Temple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Beijing’s Second Ring Road, near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many old Beijing hutongs. This area is not only a place where Beijing’s traditional sound accumulates, but also its location is an inch of gold.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order to welcome the Olympics and develop the economy, the hutongs near the Lama Temple have been demolished and rebuilt one after another.
From the auditory point of view, Lama Temple Street, which runs from north to south, is the “magic Street” of this area, and is the best footno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ity. Choosing any hutong entrance from east to west, walking 10-15 meters inward, Lama Temple Street’s noisy traffic and business sounds turned into quietness and peace in a blink of an eye. This is an urban acoustic environment that changes drastically in a narrow geographic space. The narrow alleys, the production axis of urban sound in the pre-industrial era, have now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mufflers” for dealing with the noisy traffic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narrowness of Hutong creates a business and community form different from Lama Temple Street, and also presen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coustic environment. Bicycles and tricycles, the most common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Hutong, undertake most of the daily transportation and commercial functions (coming to and from get off work, delivering beer, groceries, collecting tatters, delivering newspapers, etc.) and constitute the main body of the acoustic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Hutong is also a traditional community space. The public sound of the hutong partly overlaps the sound of the private living space of the residents—children frolicking, adults scolding, kitchen cooking and etc.
But here is the lowland of capital and the lowland of urban life. I love the tranquility of the hutong, but I can’t assume that I live in the same embarrassment as most groups in this hutong. The people in the hutongs of the Lama Temple area are not as nostalgic as people think. Many people look forward to leaving the narrow and run-down hutongs, and their residences are within the scale of the protected area on the government planning map. This is a paradox, an isolated island, day by day, for them, the tranquility of the alley sounds is too cheap. And in this city, there are many such magical streets. I can only walk many times in Lama Temple and the hutongs near it, using headphones and microphones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is city’s micro-geographical changes.
There have been too many criticisms of the fractured changes in the city, which has degenerated into an irresponsible nostalgic mood, and then evolved into an insulating, cold and high moralism. I can‘t complain that on the long list of most people’s urban survival needs, the sound environment may only be the last item. The future of urban sound environment reconstruction can only be based on the justice of urban development itself. Such justi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en capital is trying to destroy everything with the logic of maximizing benefits, a deep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ogic can be awakened, rescued and balanced, and while allowing people to independently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mselves and the city, provide more forward-looking considerations to avoid development breaks.
The fact is that the rupture of a rapidly changing city is not just a simple conspiracy of capital and politics. This is not the whole story. Everyone is a participant in the change of the city, and everyone is living amidst contradictions. As a new settler in this city, all I can write is a private city sound map and a record about the Lama Temple area. I am just a little worried. Those forgotten city sounds, not only in the physical sense, but also cultural,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re the most subtle and fatal parts of urban changes. I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the city sheltering justice, I don’t care whether the sound is new or old, whether the decibel is high or low. Because of those ears, they will eventually be awakened.
2022.04.10
2006 “谁的乌托邦”项目 – Whose Utopia
文:张安定 Zafka
过去半年,周末间或去欧司朗Osram工厂采样。从广州通往佛山Osram的路程并不长,从广州地铁的城郊坑口站下车,顺广佛高速公路而下,二十分钟车程后,盘旋的高架路边即是Osram。
整个旅程对我来说相当迷幻。比旅程更迷幻,是Osram的声响环境。Osram美妙的混合了前工业和工业的声响环境。厂区的空间并不大,但几个不同空间的声音反差和融合却相当有趣:厂区墙外有大片安静的农田,轰鸣贴墙而过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厂区内,不仅有标准的工业流水线车间,同样有紧凑的庭院,大片的草地,因为三班倒工作时间而依序空荡的宿舍,食堂。这些空间紧紧地镶嵌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就同时发生在这样一个复合空间之内,它们一起构成了听觉上的Osram。每次在工厂的草地发呆聆听鸟鸣,耳边低轰着远处车间的噪音,间或驶过火车,前工业和工业环境声响环境交错在一起,丝丝入扣,感觉分外迷幻。
这样的声响环境让我感到了巨大的不真实。即时面对工人们,我仍然触摸到这种不真实和时刻发生的疏离感。这更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工人们的梦想混合麻木与无奈的生活,就静悄悄的发生在厂区内,我那些针对现代工业所准备的左派仇恨并没有发生效用,试图的批判抑或同情,连同他人的苦楚欢愉,比念头更快的消失在厂区内。
也就是说,在Osram样本中,我这个外来者观察者的批判早早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工人对现代工业的想象、现代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他们的乌托邦同样现实发生在Osram。残酷的是,这样的状况恰恰组成了现代性问题的一体两面,归根结底,他们的乌托邦和我的乌托邦,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看似错位的想象中,重合的都是关乎人类最终境遇的乌托邦——而这样的乌托邦,现在看来,更多的陷入了无力感的沼泽。
是的,如齐泽克所说,我们必须重新发明一种新的乌托邦——它既不是对未来的想象,更不是对过往的眷恋。新的乌托邦就存在于现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种实践就是乌托邦。
因此,整个唱片的构思,并不试图依照批判的理性去安排声响结构,而是在具象和抽象混合运用的基础上,试图印象般的涂抹出对于Osram的想象、情绪与记忆,在听觉上塑造一个乌托邦,并试图呈现以上的问题——他们的乌托邦也是我们的乌托邦。
所有素材均采集自去往Osram的路途和Osram厂区。三首曲目按照城市——工厂——产品的顺序安排。第一首城市梦,记录的是去往Osram路途,穿梭城市间的聆听和想象。第二首工厂奏鸣曲,试图还原我每每穿梭在厂区不同空间的感受。第三首是关于产品的想象,尝试在工人玩灯泡和车间流水线的录音中安静冥想。
曲目名称/时间
1. 城市梦 (City Dreaming) 18:58
2. 工厂奏鸣曲(Factory’s Sonata)21:34
3. 关于产品的想象 (Product’s Imagination)14:40
Osram China: Whose Utopia? by Zafka
I went to Osram several times in the weekends to do field recording during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trip from Guangzhou to Foshan is not very long: get off at Keng Kou metro station in the suburb of Guangzhou, drive along the Guangzhou – Foshan Expressway, and you’ll see Osram besides the spiral highway in 20 minutes.
The whole trip is quite psychedelic for me. But what’s more psychedelic than the trip itself is the sonic environment of Osram: a fascinating blend of pre-industrial and industrial sounds. The factory is not huge, but the contrast and mixture of sounds in different spaces are very interesting: outside of the factory are vast, quiet farming land and the roaring railway and expressway besides the walls. Inside of it, there are also grassland and densely organized courtyards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line workshops, as well as dormitories and dining halls which stay empty regularly because of the working schedule. All these spaces are inter-embedded into a big complex space in which the workers work and live, results in what I call the “aural Osram”. The warble of the birds on the grassland, mixed with the mumbling noise from the workshops in the distance, form a psychedelic soundscape of pre-industrial and industrial sounds.
Such a sonic environment feels radically unreal. Even when dealing with the workers, I can still touch this unrealness and the omnipresent alienation. It’s like a giant black hole – the workers’ dream and their torporific life happens in the factory area at the same time. The leftist hatred that I prepared for modern industry didn’t work, my planned critique or sympathy, together with others’ pain and joy, vanished in the factory before even a sparkle of idea.
In another word, in the sample of Osram, the criticism of me as an outsider has turned into a 100% utopia. And the workers’ utopia – the imagination that they have on modern industry and their aspiration towards modern life – is also present at Osram. What’s cruel is the fact that the situation is but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of modernity, after all, their utopia is nothing different from mine. In the seemingly misplaced imagination are the paralleled utopias about the ultimate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Such utopias, examined nowadays, more or less sank into the swamp of diluteness.
Yes, as Slavoj Žižek puts it, we must reinvent a new utopia – it’s neither the imagination of future nor the reminiscence of the past. The new utopia is now. The very practice of turning the impossible into the possible is utopia.
Therefore, the arrangement of sound structure in this album is based not on critical reasoning. I tried to paint my imagination, feelings and memory about Osram in an impressionistic fashion by using bo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materials, thus creating an aural utopia in an attempt to present the above issue: their utopia is also our utopia.
All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on the way to Osram and in the Osram factory. The three tracks are arranged in the sequence of “City – Factory – Product”. City’s Dream is about my listening and imagination when traveling between the two cities; Factory Sonata is my attempt to recreate my feelings when strolling between different spaces of the factory; the third track is an imagination of product, which aims at a state of meditation during the field recording work in the workshops and the “Playing with light bulbs” session.
Track titles / Durations:
1. City’s Dream 18:58
2. Factory Sonata 21:34
3. An Imagination of Product 14:40
Original text by ZHANG Anding (Zafka)
Translated by Lawrence Li
2022.04.03
2005 “The Political Listening of Urban Sounds”
The Political Listening of Urban Sounds Text / Zhang Anding (sound artist)
In one of my texts titled Inaudible Cities, I suggested a way of recreating our private maps of urban soundscape and rebuil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und, culture, community and the cit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sound walking”.
Listening, however, is more than that. It’s not going to automatically become a conscious and independent behaviour or the tool to re-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the city. Listening is a symmetrical game: at one side, it holds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onic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at the other, it remains critical. This is, above all, a collapse of the hegemony of listening aesthetics. It advocates a sound-oriented approach: open your ears, re-evaluate the hierarchical order hidden in your listening habits. The order is not only about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all kinds of sounds, but also the value system that they define.
Nowadays, hearing is already the principal sense that is captured within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urban soundscape. The act of this capture is merely a link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haping of urban spaces by capital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question of how is individual listening tamed and fit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should be placed into the context of Michel Foucault’s modern political discourse about body politics.
Nowadays, listening is not only about music, it’s a critical tool, because sounds manifest the justice of a city. We’ll start our reading from the basic spati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both physical and residential) of the city: the birthplace of urban soundscape.
Urban Soundscape Shaped by Capital
For many, the strongest impression left by the sonic environment of Guangzhou boils down to one word: restless. Others argue that the appropriate word should be “grassroots brouhaha”. Ask a pro-Guangzhou person, and he / she will tell you that all these disturbance can only mark the memorable fact that this is a multicultural, embracing city, the brouhaha is the evidence of its energy, which, on some level, serves as the therapy for the possible maladies of modern cities as a result of rational planning of the political power. After all, all urban plannings are about the redistribution of spaces and resources within the city.
The restless is a result of the diversity of space: business districts, residential areas and streets, all tightly cling to each other. This is indeed an aggregation of high decibel sounds. But this sort of sonic environment had found their way of fitting into the city.
The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theory tends to divide the functional spaces in a city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is kind of thinking, according to the Frenchman H. Lefebvre, is a mere technical imagination of a “pure” urban space, one that lacks political reflection. The cities which employ such a division generate various automatically pigeon-holed soundscape, for instance, the torrent of traffic noise as a result of the long distance between main avenues and the residential areas; or the lifeless silence between the skyscrapers in the business district at night.
Fortunately, this kind of pureness is hard to find in Guangzhou, whose grassroots vitality (a result of the diversity) should be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vitality of capital. Here’s a city surrounded by hills and permeated by water, one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urban area. The money-making impulse of its citizen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has rapidly changed the physical as well as resident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ut ruthlessly in other cities of China, is much less visible here. Not that there isn’t a top-down city planning in Guangzhou, but the capital is much more vehement and efficient an agent in changing a city’s structure than planning.
Compared to other cities of China, the urban demolition in Guangzhou is indeed mild. 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leftists’ urban planning theory, breakneck-speed demolition and the accompanied slogans prove but one thing: that the city space has been complete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apital recycling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the society, that the priority of the marriage of capital and political power can hardly hold the living needs from the grassroots.
The planning and positioning of many of the cities in China – embodied in slogans such as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central city”, and the derivative ones “industrial planning”, “readjusting of urban layout” and “regional re-functioning” – reflect the ambition of reshaping and fitting them into the glamourous landscape of globalization. It’s a self-explanatory ideology, but this kind of slogan-ish practice has never been fully pushed forward in Guangzhou, whose image nowadays doesn’t really meet the standards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is, however, justifies the city’s development, which is based on the spontaneous needs of its residents, without being easily overruled by the rational design of political power.
This characteristic is also evident in the realm of business. The governmental design hadn’t changed much of the urban commercial network, no matter it’s Shangxiajiu or the Beijing Road walking streets. One’s not likely to experience a soundscap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business streets in Beijing or Shanghai even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Tianhe (footnote 1). There are no reverb-friendly spaces or aptly-dense cluster of customers here, only down-to-earth trading. Hand-clapping in front of the shops – a method often used by modest little stores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passersby, a soundscape easily heard in secondary cities – finds its way into the air of the busy commercial area of Guangzhou. And there’s the second-hand markets of Dashatou, where the mixture of second-hand Mandarin and second-hand English is commonplace. By bringing home inexpensive used appliances from China, African merchants are witnessing a classic moment in the link of global trading together with Guangzhou.
The Sound History of Migrants
The diversity of urban spaces in Guangzhou coincide with its number of migrants. The low cost of life and the role as the world factory has resulted in another son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city: the diversity of accents.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have brought all kinds of accents with them. Together with the 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y have invented the largest sound toy of Guangzhou: Urban Villag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uildings in the villages – which are built by locals on their own farmland – are often within a palm’s reach. Each Urban Village is an independent eco-system, within which you’ll see daily lives,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grassroots order, in another word, the spontaneous aggregation of various context in the most limited space. Similarly, it’s not easy to find so many densely-aggregated migrants of marginal professions in other cities: flower-hawking kids, beggars (many of them already use electronic devices), pirate vendors, motor-cabbies, prostitutes, etc. And the curbside barbecue stands, which constitute the prominent tune in the nighttime soundscape of Guangzhou, are mostly if not completely migrants-dominated.
While living a hard-knock life in the cracks of the city, these migrants have altered Guangzhou’s sound environment with their own sonic identities. Such a scenario, however, is the embarrassing embodiment of the city’s justice: on one hand, the residents are bestowed with right of survival; on the other, they are suffering from inequality and the absence of urban planning.
Fortunately, the sound history that migrants created is being documented. Armed with microphones, local sound artists have recorded down the complex urban soundscape. This year in June, two of them – Zhong Minjie and Lin Zhiying – released a double-album called Suspended Spectacles. The album presents a morphing urban sonic space which is constantly reconstructing itself.
This kind of endeavour had started as early as last December, when 21floor – a Guangzhou-based open collective of which the two artists are members – organized a performance called Sonic Brouhaha at Gin Yan Club on Shamian Island. The performance was focused on the multiple 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 of urban spaces, and was implemented in a novel fashion: people with various social roles and status (public servant, professional, peasant, student, artist, worker, media worker) were invited to a typical karaoke suite – a generic internal space in the city, therefore turning the space into a miniature landscape of the city. The artists’ intention was obvious: through documenting the sound in a city, they interfered with / sampled / extended the urban space by means of sound and video, released the concentrated urban vitality within the entertaining brouhaha of the karaoke space, restored the lost locality and encouraged the subject to rethink the notion of survival.
These are only the action from the artists. Guangzhou is changing, no one knows how long will the complex but vital urban soundscape last. Nowadays the heavy industry is being rapidly developed, the capital-dominated nature of it will have absolute demand of the redistribution of urban spaces and resources. In the urban plan for the future, Guangzhou will try to extend to newer districts while maintaining itself as an “ecological city that is suitable for both living and working”.
Perhaps the residents, like locusts, will eat away their own city and the last remaining power for their ears. The city has never learnt to hide itself, it keeps its body open, grows arbitrarily, and scream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op-ed page of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Sep 4, 2006)
(Translated by Lawrence R.Y. Li.)
Footnote 1: A district of Guangzhou crammed with office buildings and malls.
2022.04.03
2005 “城市声响的政治学聆听”
在“听不见的城市”里,一次声音漫步(sound walking)练习,足以让我们开始重绘私人城市声响地图,重续声音-文化-族群-城市的藕断丝连。
但这并不是聆听的全部——它不会自觉成为一个主动而独立的行为,成为我们重建个体和城市关联的工具。聆听是对称的游戏——一端尊重和理解城市现有声响环境,一端保持聆听的批判性。这首先是听觉上美学意识形态霸权的破除——秉守声音本位主义,开放双耳,反思听觉习惯中隐现的权力秩序。这种秩序不仅指向各种声响的存在或者消亡,还指向它们所被标明的包括美学在内的各种价值体系。
如今,听觉已是城市声响再生产机制中被捕获的主体感觉;至于狩猎者,也不过是资本和政治权力重塑城市空间中的一个环节。而个体的听觉如何被驯服,被纳入主体治理框架——这个问题应被置于福柯关于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的现代政治论述中。
如今,在音乐性诉求之外,聆听要成为批判性工具——因为声响已是城市正义与否的标注。我们的解读,从城市空间基本构成(物理结构和人群结构),城市声响环境诞生地开始。
资本引导的城市声响
很多人说,广州的声响环境留给他们的最大记忆只有两个字——浮躁。但也有人说,不是浮躁,而是一种草根的喧闹。在钟爱广州的人群耳中,再多的纷扰也只说明了一个值得铭记的事实——这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喧闹标志了草根的活力,这种活力适度阉割了政治权力理性规划带来的现代城市可能病态。毕竟,任何城市规划,都是对城市空间和资源的重新分配。
喧闹来自空间的芜杂——商业区、住宅区和街道公路,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从物理上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声音的高分贝聚集,但这样的城市声响环境,由自身的存在路径。
传统城市规划理论,仰仗以交通为主轴的城市空间功能区划分路数——法国人H.Lefebvre批判说,这种抽象思维是有关“纯净”城市空间的技术想象,不具有政治性的反思。在这样的划分中,很多城市呈现被自动归类的声响——道路远离人群,只留下交通噪音的洪流;而夜晚的商业区,摩天大楼间只剩下一片死寂。
幸好,广州的空间并不拥有纯净——芜杂体现的草根活力,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活力的直接后果。广州城区面积不大,丘陵地势,依山傍水。二十多年民间的财富冲动迅速改变了城市的物理和人群结构,政府对城市的改造魔力远不及中国其他城市——并非广州没有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只是资本自发改变城市格局远比规划的推行来得猛烈和迅速。
相比其他中国城市,广州城市拆建远不够疯狂——在城市规划理论的欧洲左派理解中,疯狂的城市拆建和标榜的口号只意味着一个事情——城市空间彻底纳入了整个社会的资本循环和商品生产,资本结合政治权力的首位性,已经容不下来自草根的居住诉求。
中国众多城市的规划定位——国际性大都市,中心城市,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规划,城市布局重新调整,区域功能调整——反映了重塑城市,并将城市置入全球化光荣图景的企图。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意识形态。但在广州,类似口号的实践一直无法顺利推进——广州如今的面貌,并不全然符合一个国际化都市的形象。但正是这种不符合,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正义——人群响应自身的需求,而没有轻易服膺政治权力的抽象理性设计。
商业是另外一个例子。广州的城市商业网络,无论是上下九还是北京路步行街——政府的设计并没有改变太多,即使在天河——城市的中心商业地带,也无法体验与北京或者上海商业街一般的声响景致——这里没有空旷的混响环境,适当密度的顾客群,只有朴实的商业买卖。拍掌招手揽客——这种小门店经营的手段,中小城市常听的声响,在广州的繁华商业地带,藤蔓般顽强的生长到城市上空。还有大沙头的旧货市场——在这里,各式蹩脚普通话和蹩脚英文的混合是常态。非洲的商人们把中国的廉价二手电器直接带回了故土,和广州一起刻写全球贸易链条的经典时刻。
移民人群的声音史
与芜杂的城市空间相匹合,广州是中国最斑斓的移民城市之一,生活成本的低廉,世界工厂的位置,最后纠结为这个城市另一个声响特征——芜杂的口音。
来自全国各地谋生的人群操练着不同的方言,他们和急速城市化过程一起,成就了广州最大声音玩具——城中村。那些原是农村的地头,私建的房屋间只有巴掌的距离。每个城中村都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日常生存,商业体系和底层秩序,各种语境在最狭小的空间自然聚集。
同样,很难在其他城市如此密集的碰到这样多元化的移民人群边缘职业——卖花童,乞讨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用上了电声设备),盗版贩卖者,摩托仔,妓女等等。而半夜广州声响中的主旋律——成片的烧烤摊档,无不是移民的谋生。
这些移民在城市的缝隙里顽强生长,以自己的声音身份,改造了城市的声响环境。而这样的声响图景,却是城市正义的尴尬体现——一方面是生存机会的给予,一方面是更多的不平等和缺失的城市管理。
移民人群造就的城市声响历史已经被记载——广州本土的声音艺术家们手持麦克风,采录了城市芜杂的声响图景。今年6月,钟敏杰和林志英发表合作双唱片——《悬浮景观》,录音片段呈现的,正是一个流动的,不断重新建构的城市声响空间。
而这一努力自去年的12月就已开始——他们所属的广州开放性团体21楼(21 floor)针对城市空间的物理、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复构性,在广州沙面惊艳会K歌会所,进行了名为“众声芸说”的演出。这个计划有着奇特的执行方式——邀请各式身份不同阶层的参与者(公务员、专业人士、农民、学生、艺术同行、工人、媒体从业者等),在演出场地K房——一个无差别的城市内部空间,构成微缩城市图景/印记。
艺术家的意图非常明显——对城市声响的记录以声音和影像媒介,再次切入/截取/延伸城市空间,在K房的声色犬马空间中,将生机勃勃的城市活力再次浓缩释放,就此恢复本地(local)的在场性,增进主体的生存意识考究。
这只是艺术家的行为——广州正在改变,没有人知道,芜杂但充满草根活力的城市声响还能持续多久。如今,重工业已在快速发展——这种资本密集的产业,对城市空间的和资源的再分配有着绝对的要求。而广州的未来城市规划谋求拓展新区,并试图平衡为“适宜创业发展又适宜生活居住的山水型生态城市”。
也许,人群将如同蝗虫一样,把自己的城市和双耳的最后一点权力,一点一点吃掉。其实很久以来,这个城市并没有学会隐藏——它一直张开身体,肆意的生长,嘶鸣。
2022.04.03
2005 “听不见的城市”
全世界有太多的城市,而他们中的太多已经只会发出一个声音——交通噪音,正是这种全球同质的声音把城市的过去深深的藏了起来,而我们生活的城市,已经快“听不见”了。
意大利人卡尔维诺说,城市如海绵——“吸收着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因此他要用整本书讲述《看不见的城市》,拯救自己,拯救未曾失去的但已沉睡的可能。
而在“听不见的城市”里,闭上眼便无法分别自己究竟身处何方,更遑论顺着听觉的手纹,回溯到城市可能的历史曲幽之处。
三十多年前,声响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鼻祖加拿大人Murray Schafer已经对此忧心忡忡。不同的文化和人类生活,塑造了各种不同的前现代声响环境,斑斓灿烂,而由此出发的条条道路,却不幸通向了一个“罗马”——千篇一律的现代工业声响环境,同质而非差异,这个全球合奏的主调,也是环境声学意义上,现代性留给全人类无数双耳朵的同一病症。
声音从来就不能简单解构为正弦波的嘉年华——这只是物理学家的癖好。一个城市的声音,作为人类记忆的重要元素,没法与地方历史文化,以及族群记忆脱了干系。人类活动改变城市物理和人文环境,成就了不同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音景),曾经给了每个城市独特的标识。这些音标并不如城市公共建筑或者雕塑引人瞩目,但它们弥散,无所不在,成为这个人与城市共同呼吸的空气。
在中国,很多人怀念西湖边“柳浪闻莺”,“南屏晚钟”,怀念“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怀念“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现在,这些音景只能以视觉的方式,呈现在山水画中,任人凭悼。
如今,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吴硕贤院士说,具有“听觉关怀”的研究者们太少。中国环境声学研究严重滞后,本不多的研究者终日藏匿实验室,揣摩建筑内部的最佳声响效果,而忘却了建筑之外的广阔公共空间,中国还有亿万大众,正苦受城市噪音污染。
如今,在“听不见的城市”里,能呼吸的耳朵已经太少,姿势僵硬麻木的耳朵已经太多——所谓充耳不闻,只是生活的常态。
而聆听者的姿态,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释义和阐释情境,构成了当代声音聆听的一个潜在无法回避的前提。主动聆听是一种态度,从声音出发侦测自我和城市的关系,挖掘城市隐藏的记忆和历史,看看人群可以多么迅速的忘却最初的听觉偏好,看看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去年,在英国生活惯了的声音艺术家Scanner,在广州停留匆匆数日,最后留下的唱片,正是一个“听不见的城市”——琴瑟之声,粤语播报的岭南地名,缓慢交错,安静,但相对于广州真实的声音环境,过度唯美到能嗅到腐烂的气味。Scanner害怕极了广州的喧闹,他觉得广州“应该”是个“花城(flower city)”——安静幽密,繁花密布,一派岭南风情。虽然这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遗失太久的本地城市传说,但至少,Scanner表明了一种态度。
这种试图弥补声音—文化—当下存在的断裂,重建城市声响环境的态度,正在穿越孤独的学院围墙——还有两个月,“噪声治理研修班”全国招生第五期要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开课了。密密麻麻的课程单上,除了建筑声学,城市噪音控制同样赫然在列。
学院内的秘密噪音研修班,肩负的任务非同一般,但还远不够——治理噪音的前提,是学会聆听“听不见的城市”。通过自我认知和反思,以福柯擅长的知识考古谱系学的方法,在主流的城市声音(也就是交通噪音)统治之下,挖掘同样涌动的断层分裂的声音历史。
而环境声学将充当重建的学科工具。环境声学发端于建筑声学,而后者的兴起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巧合——一百多年前, 哈佛大学校长在讲堂的讲演,居然无法清晰传达到底下芸芸众生,助理教授W. C. Sabine只好接过任务加以研究。三年实验室枯坐后,Sabine用混响计算公式的精确抚慰了不安的人们,立起了“建筑声学”的山头。
二战后,科技、工业和交通迅速发展,尤其是汽车的日益普及,噪音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而单纯的建筑声学已经不能解答这些问题——因为一个城市的“听不见”,建筑材料以及设计的粗鄙,只能推波助澜,真正的祸首,是看不见的现代性和看得见的人类冲动。
从1974年第八届国际声学会议开始,环境声学成为了一个特定的学科术语——原来建筑物内部声学问题,扩展到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公共空间。研究的领域也从单一的物理学迅速扩展到美学,政治学,城市管理等多学科领域。
在“听不见的城市”里,我们期待,环境声学可以成为破除当下窘境,恢复城市和人群多样性,重建城市声响环境和文化血脉关联的重要手段之一。
全人类对听觉的自我拯救还刚刚开始——少数发达国家自我拯救的步伐,也快不到哪里去。调查声音遗产,保存社区声音,设计城市音景,在城市公共空间放置声音装置,也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现实有些残酷,但还有人苦中作乐。
三年前,瑞典维多利亚学院的几个家伙,开启了一个“声音城市(sonic city)”的项目。他们的作品是一件神奇的衣服,他们的野心足够大,他们的想象力,是要把我们生活的城市声音,实时的融入音乐。
设想一下,穿上他们精心设计的衣服——尽管在重量上,它走在了时装的反方向,但是只要你漫步在城市,向左或是向右,城市贡献的每一个声音,通过随身的麦克风,转化为信号进入电脑,一番参数演变之后,你耳边呈现的已经是已经音乐化的城市声音环境。
这也许是借助科技的听觉乌托邦,但既然城市已经“听不见”,一些更low-fi的办法可以用以实践——把自己的耳朵变成调频电台,自主的选择城市声音,当一个自由的指挥家,在每一次行走中编织自己的声音世界。这种成本为零的修炼,Schafer称其为“声音漫步(sound walking)”。
下一次,我们且端起耳朵,听听我们生活的城市,每个声音都在讲述怎样的故事。比如在南方,在广州,城市声音斑斓浮躁,草根气息强烈,如同这个城市的历史,从来没有学会隐藏。